回首中文系
——石鵬飛教授訪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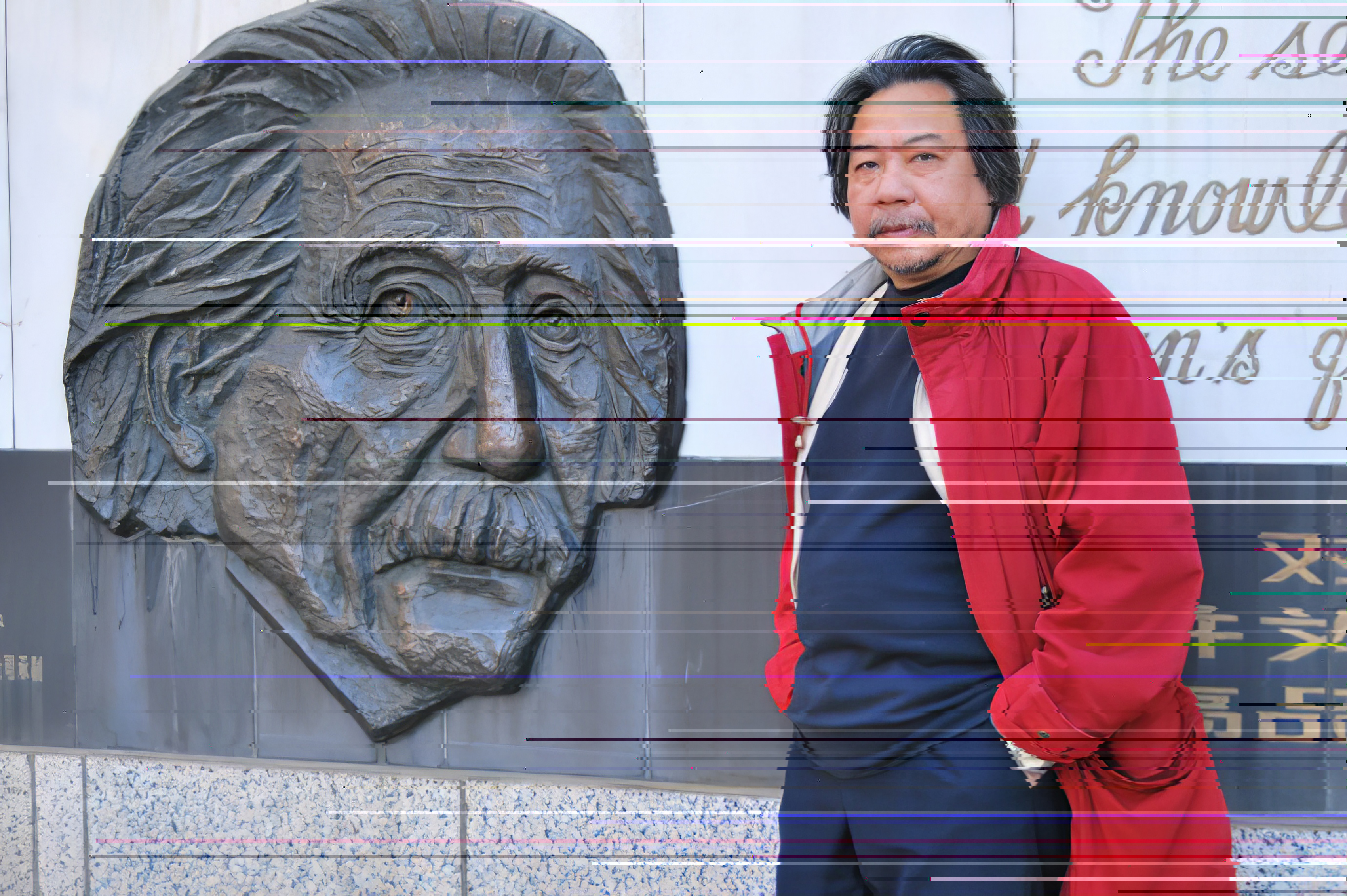
采訪人:高田雪、鐘銀燕、袁若愚、邢舒涵
時間:2021年3月5日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龍泉小區業主委員會辦公室
石鵬飛,教授,1977年考入雲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曆任雲南大學職業與繼續教育學院教授,《雲南大學報·成教版》主編,雲南省詩詞學會副會長,2009年被聘為昆明市文史館首批館員。
采訪者:石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石鵬飛:你猜猜我今年應該幾歲了?我比共和國大一年,48年是我的生年,74了,對吧?前兩天你們采訪的李炎老師,在我來看是小輩,他現在還在任上,我退休都已經有十四年了。我是48年生的,68年20歲的時候就從上海到了雲南西雙版納當知青去了,在西雙版納當了九年知青,就考上了雲南大學。
采訪者:我們想請問一下您,您當時是文革結束恢複高考的第一屆?
石鵬飛:第一批,标标準準的老三屆。那是67屆高中生,而且我在上海的學校是名校。上海曆史上最好的大學是聖約翰大學,複旦那時候還不上榜,聖約翰大學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我是聖約翰大學附中的,光校友當中就産生過共和國兩位副總理,還有三十位兩院院士,貝聿銘也是校友之一。我高中是67屆的,也就是“老三屆”。高中畢業後,我來到雲南西雙版納農場待了九年,随後考上雲大中文系,當時的錄取率是5%。本科畢業後我留在雲大成人教育學院任教。
采訪者:我們想請問您,當年是哪些原因讓您選擇在雲南大學?
石鵬飛:我是上海人,當然首先想考回上海去,所以我的第一志願是複旦大學中文系。第二志願才是雲南大學中文系,第三志願是一個師專。最後複旦沒有錄取,雲大錄取我了。至于為何考中文系,我從小就喜歡文學。我是上海人,喜歡聽評彈,起先喜歡聽評話。評話都是大書,所謂大書,即隻有說沒有唱,比如說嶽飛、三國等曆史之類;到後來又喜歡聽評彈,是既有說又有唱的。評彈的比較抒情,蘇州人唱的都是吳侬軟語,非常好聽。起先我聽不懂,到後來拿個唱本,一看上面全是七言詩。比如有一個曲子,“香蓮碧水動風涼”,也是七言詩。我自此開始喜歡唐詩宋詞,并也開始就喜歡小說、散文,所以到後來對中文産生學習的欲望。在農場裡的九年日子艱苦,靠什麼東西來擺脫自己的苦惱?就每天晚上堅持讀四個小時的書,從點油燈開始,一直讀到我們農場裡面安裝了發電機,國家把電網拉過來,我們自己有了電,從晚8點鐘開始讀到12點,堅持若幹年當然有好處的。那時書也很少,隻有馬列毛的著作、魯迅的著作以及《紅樓夢》。唐詩宋詞也是找着看,很多書都不合時宜了,那順便拿的一本來就手抄。記得當時還曾經有個想法,想編本《唐詩宋詞字典》,幹嘛?第一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素養、文學素養,第二個是打發光陰,消磨時間。要不然這四個小時怎麼過,對吧?所以這樣對文學的愛好就更深了。後來,到了填報志願的時候,當然首屈一指的肯定是複旦中文系,要麼就是雲大中文系。複旦全國著名,那現在雲大全國也有名了。高考我考語文一半小時就考完了,還有半小時就在操場上溜達。後來聽中文系的招生的老師告訴我,他們發現給我的作文分數打低了,最終給省教育廳打報告重評。總之我身上的文學情結還是很濃的。當時為什麼會跑到雲南來呢?兩件事情,其一,中國著名的四大散文家之一的楊朔寫過一篇《茶花賦》,裡面有一句話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一腳踏進昆明,心都醉了”。像現在北方還在冰天雪地,冷山瘦水的時候,昆明已經豔陽高照,氣溫宜人。其二,當時有一部《美麗的西雙版納》的紀錄片,也吸引了我到雲南來。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原因,但這很重要。這些作品裡邊有文學因素,“一腳踏進昆明,心都醉了”這句話現在還變成昆明的廣告語了。喜歡文學到後來當然也不僅僅是搞文學,我感到文學也太窄,最終走向搞文化了。喔,你們随時都可以插話,我講課的時候學生都可以插話,甚至還可以反駁我。
采訪者:也就是說正因為您對文學的喜愛,才和雲南大學中文系結緣。想請問一下,您在雲南大學的求學經曆中,有哪些給您印象深刻老師和課程?
石鵬飛:第一位是趙浩如老師,就住在我們小區裡面,現在是中國當代著名書法家。我喜歡唐詩宋詞,但并非出身書香,我的父親是初中畢業,我的母親是小學文化,能識字。為什麼說趙老師對我有影響?因為趙老師可以說是我的領路人。來雲大以前我隻知道中國文學好,最多也就看一些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來到了雲大中文系讀書,講中國文學史就是從先秦兩漢開始講起,趙老師應該是我的中文入門的領路人。要知道,唐詩宋詞以前并不是一片荒漠,而裡面也照樣是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照樣是處處動人的。趙浩如老師比我大10歲,今年已經84了。
跟你們講講系史吧。張文勳老師當時是我們的系主任,如今也住在我們的小區,已經是95歲了。我們三個人好像是個梯隊,他大趙老師10歲,趙老師大我10歲。張老師跟我們講中國古代文論,也應該算是我的領路人,他也是雲南在文學界和文化界當中很出名的一個人。
還有一個,趙仲牧老師。趙老師跟張文勳老師是同學,可惜他已經去世了。趙老師思辨色彩很強,擅長條分縷析。分析本身就是科學的一個前提,什麼叫科學?就是分科學。趙老師有很高的哲學智慧。
第四位是吳進仁老師,安徽人,劉文典先生的關門弟子。他給我們講的古漢語,聽吳老師的課很讓人佩服,完全像一個“兩腳書櫥”,文學的天上地下無所不曉、無所不知。他現在也去世了,沒去世的時候有時候在馬路上見到他,嘴巴裡總是念念有詞,在幹嘛?背書。你問他一句什麼内容,他馬上一串一串地應過來。還有很重要的一條,他在跟我們講古漢語的時候還講了音韻學。我這兩年一直在搞小學,所以吳老師也是我的領路人。古今語言的語音是變化的,古人的嘴巴沒有今人的嘴巴巧,所以重唇音到後來才慢慢變成了輕唇音。前兩天我在小學裡還開了個講座,講《漢字的前世今生》。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左字是左手嘛,左字,甲骨文就寫成左手,右字是右手,甲骨寫成右手,兩個字就是兩個手。左字加個單人旁,就是輔佐的“佐”;右字加個單人旁,就是保佑的“佑”。都是幫忙的意思。但是為什麼左字底下是“工”,右字底下是“口”呢?這個挺有意思,說明有尊卑之别。左手的“工”像是别人拿來一個工具伸手過來幫你,代表人助;右手的“口”代表禱告上天,是神助。右邊通常是主要用力手,人是重右輕左的。
你說人站起來,兩條手伸開,兩條腿叉開,這不就“大”字嘛?為什麼我們後來把大字就變成大字,人字就變成人字了?其實是一個正面形象,一個側面形象而已,本來是一個字。這個就是文字學。所以吳進仁老師、趙仲牧老師、張文勳老師,還有趙浩如老師,都應該算是我的領路人,我對他們印象還是很深的。當然我自己是有學科傾向的,我偏重于搞中國古代文化。所以對其他的老師們可能印象也就不是很深刻了。
采訪者:您在雲大中文系短短幾年的求學經曆。對您的整個人生有什麼樣的意義?
石鵬飛:我是1977年底考上大學的,開學是1978年2月份。所以這一年是很特别的。前三年我是在雲大中文系讀的,第四年時,雲南大學推行了一套政策,就是把一些讀書讀得好的學生送到外校去,便派我到四川大學中文系去讀,讀什麼?專攻蘇東坡。因為川大中文系整體質量要比雲大中文系高。川大中文系有兩個寶貝,第一個是杜甫,第二個就是蘇東坡了。所以我最後一年實際上是在川大讀完的,也就是說我提前留校了,但是還沒有提前畢業。我跟着川大中文系的77級學生一起讀,讀完一年以後參加他們的考試,學分都認的。後來我就回到雲大來了,在成人教育學院任教。這個政策很好,因為學校裡邊需要補充一大批高校老師,但是研究生剛開頭,招的非常少,所以就讓尖子生出去學習一年,現在看來有點像訪問學者一樣。當然我們也談不上學者,我們當時還是學生。
我讀書期間是敢挑戰權威的。我跟你們說個事情好了,一年級的時候有寫作課嘛,我把作文交上去了以後,一位老師把作文批下來,我一看批語,他壓根就沒看懂吧,我就寫對批語的批語給退回去。于是被寫作教研組的組長、副組長狠狠地批了一頓,一年級那麼狂,四年級不得了。我當時隻有大一。現在張文勳老師見到我還常常講,石鵬飛是非常個性的一個學生。
至于我從教以後的經曆那就多了。因為我在成教院嘛,成教院教書都是教成人生,年紀跟我差不多大。我當時34歲,他們也是34歲上下,有的還比我大。我入職成教院後備了一年的課,就開始給他們講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這個是最難講的。《紅樓》《水浒》《三國》《西遊》,你拿來讀,至少六成、七成,你們是看得懂的。但《詩經》如果沒有借助字典,沒有人輔導的話,就是大學生也讀不懂。什麼叫“關關雎鸠,在河之洲”?什麼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們那些學生比你們要老辣得多,因為都在社會上泡過,年紀都跟我差不多已經搶到工作了,已經搶到位置了,唯一少張文憑。如果跑到本科裡面去拿文憑,他的工作就沒有了,位置就被人家搶掉了,再加上有的都已經成家立業,有老婆生孩子了,要養家糊口,考上日制,工資也沒有了,所以全跑到成教院了。那個時候他們的素質要比你們的素質還高。他們最初要反對我,要把我轟下台,他們說雲南大學成教院糊弄人,怎麼找一個畢業才一年本科生進來,教我們中國文學史先秦段。但是講了一兩個月後,我收到一封匿名信,不是罵我的,而是誇我的,說我的課講得好,是知識青年的驕傲。這樣我就有底氣了。我于是去查一查到底是誰寫的,如果罵我的我查,這樣就不講師德了。最後查出來,是來自雲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個學生。這樣我就有底氣了,就開始有點“張狂”了,所以上課的時候就講了一句,你們不要天天去歌頌得了諾貝爾獎的英雄,你們要是能夠發現他以後可以得諾貝爾獎,那才叫做慧眼識英雄。我還講了一個比方,不要一天到晚去歌頌長江,應該去歌頌在崇山峻嶺當中努力掙紮奮鬥的金沙江。後來他們給了我個綽号叫“金沙江”。

(講座中,石鵬飛老師供圖)
第二個事情就是開講座,93年雲南大學成立東陸講壇,當時的金子強老師叫我去開個講座,讓我也講個題目,把小年輕全震倒了,什麼題目知道嗎?《改革大潮下的現代婚戀觀》。那天我去講,在在北學樓階梯教室。我7點1刻進去的,樓道、教室裡全部都擠滿人。我說:“你們要讓我進去,你們不讓我進去,今天你們白來。”他們說:“你就是石老師?”我當時的名氣在成教院,在日制生之間是沒有名氣的,他們是沖着這個題目來的,這個題目太震撼。進去了以後我發現左右前後全是人,他們給了我把圈椅,我連黑闆都無法轉身去寫。我的夫人要進去聽我的課,她是7點鐘進去的,根本找不到位置,進去站在過道的人群裡面,穿着高跟鞋足足站了兩個小時。後來站不動了,怎麼辦?脫了高跟鞋站在地闆上。那場講座掌聲、笑聲不斷。所以到後來有人寫報道的時候,說石老師那個講座真是奇葩了,兩小時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跑掉。怎麼跑?那架勢完全像春運高峰擠車一樣,前胸貼後肚。這一講了以後,全校轟動。一半贊成,一半反對。你們的日制同學給了我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綽号,就叫“鐵嘴”了。後來,我陸續講的主題有死亡,有宗教,講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基因,講了傳統文化,也講了女權。97年《女人的發現》是我最後一次演講,有人說女人都存在,還需要發現嗎?你們是否思考過什麼叫“女人的發現”?那個時候聽晚7點半的講座,有些學生甚至中午12點半就進去把位置占住了,礦泉水、面包圈全部都帶進去了。還有些學生是吊在窗台上聽完的,就像鐵道遊擊隊一樣,爬火車吊在窗台上。這個是我記憶非常深的東西。為什麼成為“鐵嘴”?就是這樣來的。我以前跟日制是無交集的,隻教成教;後來就開始開校選課了,我96年開了一門《老子研究》。一挂牌,教務處打電話過來,說613個學生選你的課。我說這可怎麼講?他說到慶來堂去講。我說你尋開心的嗎?等到我改卷子時,真是“愚公移山”,後來分了三個學期把這批學生消化掉,一個學期200多個。200人我就感到頭大的不得了,因為我有看法:講課是炒菜、監考是等飯吃,改卷子是洗碗。有道理吧?講課是展現我才藝的,那當然是精神抖擻,而且一到課堂裡面去,就像戰馬聽到槍炮聲一樣,鬃毛全都豎起來。監考不是等飯吃嗎?老不到時間,你說是不是?而洗碗就太沒有味道了,看來看去都是看自己的回聲。
其實我在東陸的故事多了,随便跟你們再講一個。現在是百年校慶了,在70周年校慶時,要搞一個校史展,我是副組長。我那個時候一文不名,是個普普通通的布衣老師。到了80周年校慶校史展,我成主策劃。還有雲南大學搞校園文化,當時我跟金子強老師聯手在教代會上發了一個提議,要求提升雲南大學的校園文化。後來校方也非常重視,成立校園文化課題組,我是校園文化課題組裡面的一個主要成員,搞了一本書,叫《UIS——鑄造大學之魂》,得了省教育廳的德育特等獎。現在的“會澤百家,至公天下”就是我們課題組組織搞出來的。什麼叫做“會澤百家”,什麼叫“至公天下”?等一下我要說的。到後來我又跑到江岸小區打造社區文化建設,也跑到瀾滄江水電公司,去搞他們企業文化建設。所以現在人家問我搞什麼,我說搞文學太小了、太窄了,還是要搞搞文化。
采訪者:您算是目前雲南大學的元老級教授。
石鵬飛:也不能叫元老級教授,雲南大學都已經100年了。我們這一批人經曆比較奇特,老三屆受過傳統的教育,然後到農村裡面去打磨九年,不得了,真是對我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影響是極大的。可以說,我是在西雙版納的茅草屋裡邊形成我的三觀。
采訪者:請問一下,您一直堅守的教學理念是什麼?
石鵬飛:我強調大學老師應該具有四個素質,第一個是德,第二個是學;第三個是識,第四個是才。德是什麼?當然就不是在課堂裡不抽煙了,馬路上不随地吐痰了,但這也都是屬于小德,對不對?孔子在《論語》裡面講:“賢者識其大”。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吃起飯來了浪費得不得了,叫“食前方丈”,一桌子全是菜,吃不完就倒掉了。如果在這個地方去摳文天祥,那民族英雄也當不成了是吧。我們不能一天到晚老盯着那小的地方去看。什麼是一個老師應該有的德?幾句話:追求真理、發現真理、捍衛真理、講真話。所謂德就是在這。第二個,學問要開闊,要廣博、厚積薄發。第三個要有見識,不能一天到晚淨把陳谷子爛米炒給學生,要講些人家心中所想、嘴中所無的東西,講些人家不了解的東西。所以見解一定要新鮮,新鮮了以後再追求深刻,像達爾文發現進化理論,哥白尼發現日心說,弗洛伊德發現力比多。至于才,作為老師來講,第一,口才要好,但有些人口才好,筆才不行。第二個,還應該筆才好。人家說鐵嘴,說明我的口才很好。至于筆才,我現在每天起來最起碼要寫500到1000字,我自己有個座右銘叫“不讓一天白過”。魯迅先生講,要把别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做學問上。如果今天我寫不出文章來,我會特别的沮喪。等到我把文章寫完了以後,一天感到特别的充實和飽滿。這些就是我想一個大學老師應該具備的素質。我們大學老師應該堅守一個信念是什麼?其實這恐怕也就是刻在我們雲南大學的會澤院底下的“會澤百家,至公天下”。“會澤百家”,講學問要開闊、廣博。“至公天下”,就是講你對國家、對人類、對民族、對社會要有一種關注,你要關注人類、社會、國家的命運。這也是我希望我們的學生所能做到的一條。所以中國古人講知識分子,四個字兩個詞:道德學問。如果老師不能信守自己的底線、不能信守真理,那能叫老師嗎?這種老師我就認為就絕對是個牆頭草。
采訪者:我們了解到您之前就有一本書叫《石鵬飛語錄》。
石鵬飛:對。《石鵬飛語錄》實際上是在八九十年代寫的,我把上課的時候産生的一些思想的火花記錄下來,然後找了我的一個學生畫畫,配成漫畫,我說叫“漫話”,他畫叫“漫畫”,所以叫《漫話漫畫》,後來的《石鵬飛語錄》,實際上是《漫話漫畫》的2.0版。有人就說石老師當時在課堂裡講的有很多話,後來都成了段子在校園裡面流傳。打個比方,婚姻是不是愛情的墳墓?後面我就跟了一句,“但假如沒有婚姻,愛情将死無葬身之地”。再比如說,找老婆要找三點,有點姿色、有點風情、有點思想,風情是要褪的,姿色是要老的,唯有思想是越沉越香的。這本書到2015年的時候還得了個“雲南十大好書”。我是民主黨派的,民盟的《群言》雜志連載了将近150多期《漫話漫畫》。

(教授黑闆報,石鵬飛老師供圖)
采訪者:在您退休之後,您在江岸小區創辦了教授黑闆報?
石鵬飛:93年的時候我搞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情,成為雲大校史展的副總策劃了,第二個就是開了講座。當時我們正好搬家到江岸小區,校工會就給了我一個弼馬溫的小官當當。我在雲南是屬于标準的“三無教授”,第一,沒有任何研究生;第二,我基本上不申報課題的,隻寫自己想寫的東西;第三個、是沒有任何官銜的。我最大的官銜就是江岸小區的“保長”,龍泉苑的“副保長”。我還是感到人家看得起我,我就還是想把那個事情做好,想了半天,就搞了一個黑闆報,面積很小,從95年一直出到04年。還找了幾個夥伴,其中包括以前雲南大學新聞專業的元老,我們就搞了一個所謂的“教授黑闆報”,沒想到這個教授黑闆報甚至還驚動了中南海的眼球。教授黑闆報每個月出一期,就拿粉筆抄。學校裡面給我們唯一的資助就是搞了一塊牆報之類的東西,其他就沒有了。每次出牆報,三四個人就開始用筆畫、用筆寫,下雨了就到旁邊去躲躲雨,出太陽就頂着草帽。搞了四十多期以後,昆明《春城晚報》首先報道,說是我們江岸小區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我們搞這個小報宗旨很簡單,就四句話:通情況、連感情、揚正氣、糾歪風。人家說石老師,你吃飽了撐的,你大材小用去搞這些東西,人家老頭、老太太搞的那些東西。但正像剛剛我說的,知識分子要成為社會良知,後來沒想到一炮而紅。《春城晚報》寫了文章以後,立馬就被香港的《大公報》轉載了。到後來有關方面都非常重視,于是乎,就開始以江岸小區的“教授黑闆報”為契機,打造江岸小區的社區文化的行動。
2000年的時候,8月12号北京新華通訊社新聞信息中心開了一個專題會,專門讨論把江岸小區的社區文化,把它稱為“江岸模式”“江岸現象”。不僅僅是雲南的媒體了,全國的媒體都在報道。後來我精力衰退,不想再編牆報了,也搬家到了龍泉路雲大小區。
搬到這以後,他們又叫我搞,就開始鳥槍換炮,就變紙質版的《龍泉苑》,現在辦到168期了,每個月出一期。中新社專門寫了一篇長篇文章,講一個教授堅持了25年的社區文化建設。這個就是我所謂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很重要一條,要變成社會良知的呼聲。小報如今變成了我們小區的一張名片。回過頭來講,我這一生,教書不用說了,要不然怎麼會叫“鐵嘴”;社會良知就是辦報,在小區裡面開展社區文化。
采訪者:您覺得雲南大學,尤其是中文系培養的應該是什麼樣的學生?
石鵬飛:我想咱們還是扣着校訓講。“會澤百家,至公天下”,首先學問要好,出類拔萃。第二個,你要成為社會良知的傳聲筒,成為社會良知的一個代表。知識分子不能隻是講前面半截的話,中西之間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差不多,中國人講知識分子,就是講道德學問。西方是把知識分子界定為兩個定義,第一個定義是知識載體,第二個定義是社會良知。所以愛因斯坦講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這裡面我們可以體現出來他們對知識分子是怎麼定義的:“一個核物理學家如果不在反核宣言上簽字,那就不配當知識分子。”一個核物理學家他既然能開發原子彈,那絕對說明他是知識的載體;但是他必須在反核建議上簽字才能守得住人道主義的底線。所以,我想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應該從這兩個角度去。我希望我們雲大中文系的學生,一個就是在自己的學科領域當中能夠出出其類,拔其萃,很難有人跟你比肩。第二個,你要變成社會良知而呐喊。
采訪者:随着我們雲大快要進入百年校慶的籌備階段,我們的中文系也到了百年慶典的時刻。我們想請您為中文系今後的發展來提一點建議。
石鵬飛:我們大家都說中國最好的大學第一個是20世紀初期的北京大學,第二個是20世紀中期的西南聯大。咱們向北大、西南聯大學學習吧,更多點學術自由,讓我們的學生能夠思考、能夠表達。當然自由思考、自由表達也不是随随便便的。知識分子最重要在于講道理,你必須講出道理來。前不久我看了篇文章,講中國人多是詩性思維,西方人多是邏輯思維。你們去看看古代西方的學院門口挂塊牌子,“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内”嘛。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幾何學是講道理的,“已知”“求證”“證明”,任何一步後面都有個括号。道理是什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同位角相等,如此等等。有人說北大之所以能辦好,就是因為蔡先生提出兼容并包,學術自由;西南聯大之所以辦得好,也是因為堅持了現代大學制度。
現代大學制度當中有幾根支柱,第一根支柱是教授治校,治校教學有質量。第二條是學術自由。第三條是講通識教育,也就素質教育。第四個就是學生自治。西南聯大裡面有很多學生社團,他們是很奔放的,也是很自由的。但是我認為現在大學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讓我們的學生、老師能夠有更多自由思考和自由表達的機會。但是這個自由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不是胡說八道,不能随地大小便,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自由前提就是要講道理。這就是我對中文系的學生的希望和要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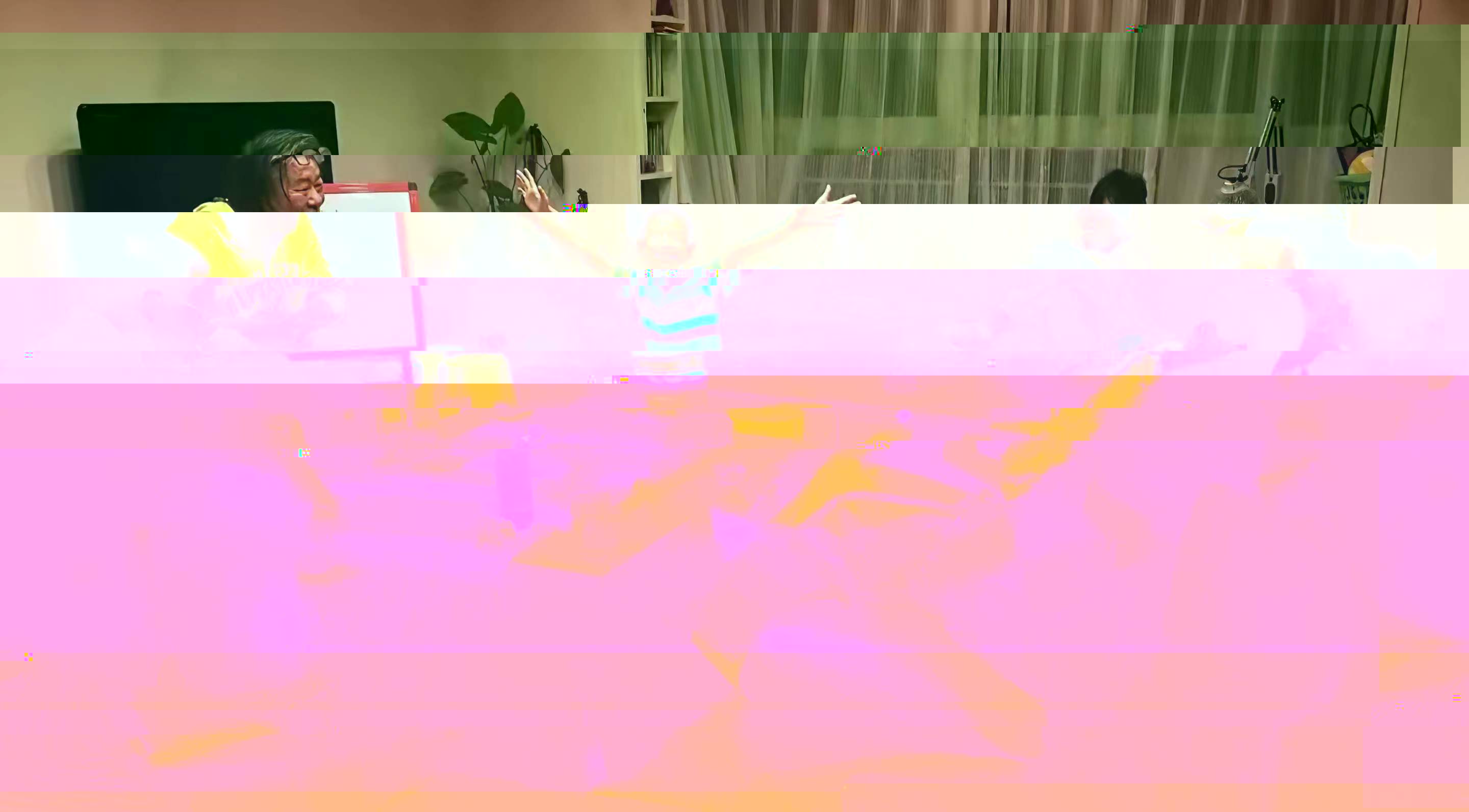
(給孩子講《說文解字》,石鵬飛老師供圖)
蔡元培當時搞學術自由的時候,你是講中文的,既可以講知乎者也,也可以講的了嗎呢;你是搞哲學的,你既可以講你的唯物論,也可以講你的唯心論;你是搞經濟學的,你既可以講看得見的手,又可以講看不見的手;你是講倫理學的,你也可以講樂觀主義,也可以講悲觀主義。看看我們的先秦諸子,孔子講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老子講是“絕學無憂”;莊子還講人生有涯,知識無邊,以有限的人生追求無邊的知識,殆矣。這就有了我們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輝煌。我希望我們中文系也有大輝煌、有大燦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