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之光照亮人生道路
——于堅訪談錄
采訪人:鄧萦夢、畢曉蕾、何子怡、李樂思、房夢蝶
整理人:房夢蝶
時間:2021年16:30—17:40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東方書店

詩人于堅(圖片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
鄧:于堅老師您好!
于:你們好,你們都是雲大的學生嗎?
鄧:是的。這是畢曉蕾、何子怡、房夢蝶,我們四位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學生,李樂思是民俗學專業的。很高興您能接受我們的采訪,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首先想問一下您為什麼要創建銀杏文學社?
于:這個說來話長,我還沒有進大學之前,我是在昆明北郊一個工廠當工人,我們那一代和你們不一樣,我們考進大學的時候,我們都已經20多歲了,比你們年紀還大。我們的青年時代,雖然是文革時期,很多書已經被封掉的,燒掉的,基本上沒有書看,但是地下也還是會秘密地流傳一些古代的、西方的好書,那時候我通過我表哥、表姐、朋友秘密借到一些西方文學作品,裡面提到那些詩人、作家青年時代組織沙龍、文學社讨論文學很向往。印象最深的是一群法國作家聚集在左拉周圍,結成了“梅塘集團”。沒進大學之前,在校的一些喜歡文學的同學已經知道我,那時是沒有文學刊物的,沒有發表這回事。我是把詩寫在手抄本上,畫一些插圖給我的朋友看,他們就傳開了,可能他們覺得寫得不錯,就從工廠傳到雲大去,中文系一些喜歡詩的人就知道在北郊工廠裡面有一個寫詩的工人叫于堅,所以我進學校之前他們就已經認識我。考上雲大後,中文系77級、78級學生,那是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辦了一個文學刊物叫《犁》,我馬上就成為《犁》文學社的成員之一。那時候發表學生的作品都是油印的,自己刻蠟版,刻蠟版就是一個蠟版,然後用鋼筆在上面刻,刻錯的地方,就用一個火柴剽一下,它就化掉消失了。《犁》隻出了一期就不準再出,那個時代,這是非常敏感的事。系領導在全系大會上,點名批判《犁》文學社,還專門點我的詩,說我的詩非常陰暗。昆明大觀樓長聯那個作者孫髯翁寫的詩都比我的要開朗。我發表在《犁》上面的一首詩是叫做《滇池夜景》其中有兩句“現在是絕對地黑暗,我劃着孤獨的小船,世界在我的心中,生命在我的漿上。”他認為這是不健康的、陰暗的,今天你們可能覺得不可思議。《犁》停刊了。但是那個時候中文系熱愛文學的同學私下互相都知道,交流作品,大家都很想再辦刊物。77級、78級畢業後,我和同班喜歡文學的同學,在學校裡面找了一個舊黑闆,用三輪車拉到通往食堂的路邊,用鋤頭挖坑,把那個黑闆立起來,然後自己買了白紙,很大的白紙,把我們的詩散文用鋼筆抄上去,貼在黑闆上。很多同學吃飯路過都會看,看的人太多了,在學校裡面影響很大。那個黑闆上的詩發表以後,就有很多其他班熱愛文學的同學加入進來,我們就認識了,有81級的、82級的、83級的,大家就商量讓我搞一個文學社。我就去找了當時中文系的系主任張文勳先生,張老師非常支持。那個時候已經是《犁》停刊快兩年了吧。那些《犁》的成員都已經畢業,他們在畢業的時候遭到懲罰,被分到不好的單位。那時候比如說在政府裡面,就是好的單位,如果你去教書或者是到昆明,外面的地方就是被流放一樣,他們都被發配到昆明郊區的學校裡面去當老師。他們畢業了,那我們還要搞下去的,我們就去找張老師,張老師就堅決支持。但是呢,有位領導反對,不高興,他說這個于堅,畢業的時候要好好收拾他。但是張老師也是領導,是系主任,他不好公開反對。中文系就批準銀杏文學社成立了。雲大有很多銀杏樹,秋天整個校園都飄滿了銀杏葉,我們就用“銀杏”來為文學社的命名。成立的那天晚上教室滿地都鋪着銀杏葉,一下午所有的社員,男生女生都去撿銀杏葉。桌子上點着蠟燭,這都是我的主意。來了許多老師支持我們。我可能是文學社裡面年紀最大的一個,比我大的人都畢業了。他們說我應該是社長,但是我不喜歡行政職務,我喜歡當一個主編,所以我就沒有當社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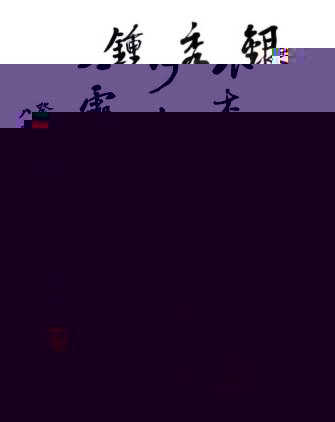
張文勳老師給銀杏社的題詞 (圖片來源:謝竺軒提供)
于:現在辦《銀杏》就好多了,學校每一期都給一點經費,夠你印刷這個刊物。那天晚上結束後,月光照耀着會澤院,那真是太美好了。你們這一代人太悲慘了,搬掉了,我能夠一直寫到現在,不過是因為我是在會澤院的教室裡面讀完的大學。那是真正的大學呵,多年後我去巴黎,索邦大學似曾相識,我們這個大學是20世紀初照着法國的大學設計的。會澤院石頭樓梯上去,左手邊靠北第1間就是我的教室,教室外面就是映秋院。林徽因設計的映秋院。我每天都能看見,窗戶外面是一束海棠,春天的時候海棠可以伸到教室裡來。我是在那樣的教室裡面讀完的大學,感覺好像就是在一個中世紀的古老大學裡面讀書。二樓就是校長辦公室,我們也可以去校長辦公室,與趙季校長說話。會澤院對面那個小樓,就是劉文典呆過的那個小樓,老師經常在2樓開會,1樓是收發室。那時候的大學,它還有傳統的、古老的那種大學的味道,有那種風氣,所以這個文學社的成立也是順理成章的。那個晚上銀杏文學社成立後,我們在月光下從會澤院的石梯上走下來,沿着學校大門左邊那個小巷,那條小巷子通向圓通動物園,叫做丁字坡,坡底有一個小吃店,古老的小店,那個小店的案闆裡面永遠在賣豬頭肉。在一盞燈下面,有一個頭有點秃的中年人,他在那裡支着一個很大的案闆,一排銀子般亮的切成片豬頭肉就躺在那個案闆,買一盤豬頭肉,大家喝點小酒,慶祝我們偉大的文學社的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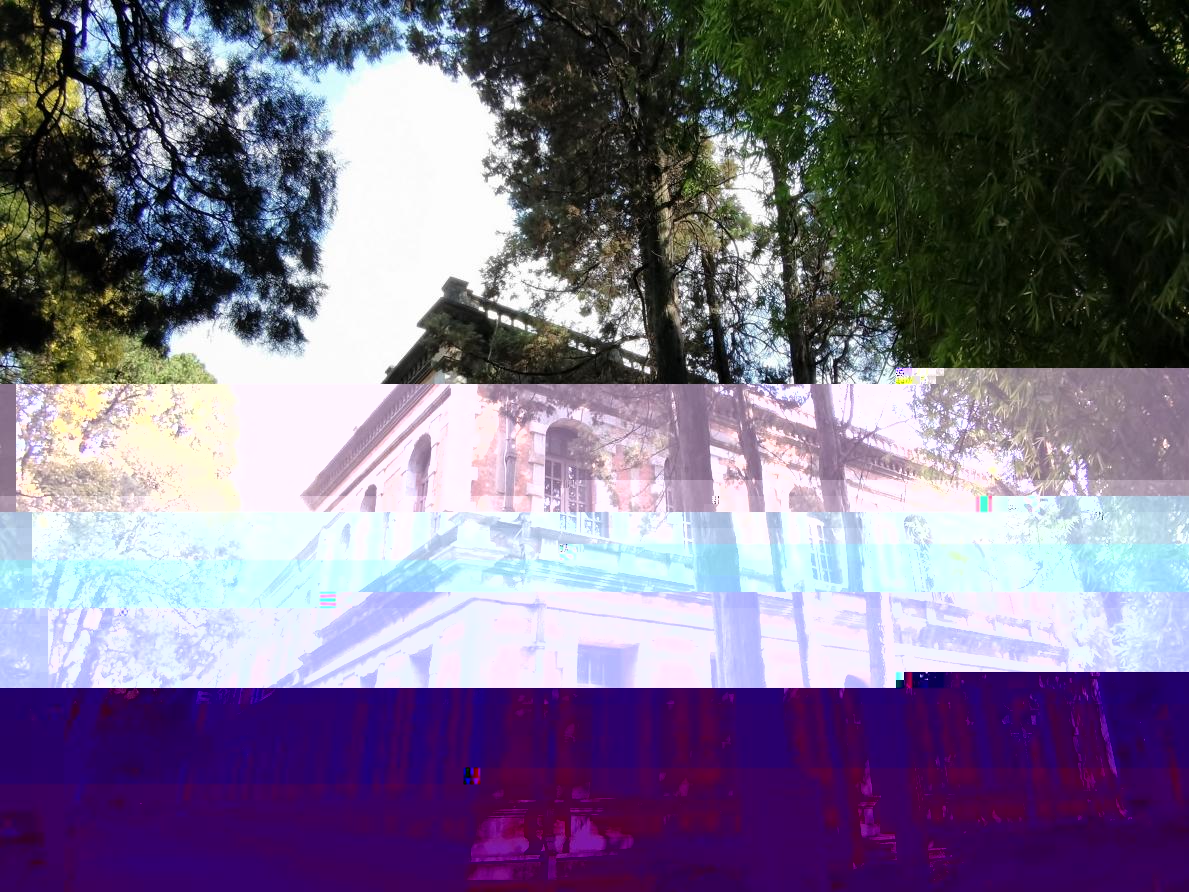
雲南大學東陸校區會澤院 (圖片來源:王雲杉提供)
鄧:您是文學社最重要的人物,那我們就想問一下,您最開始成立文學社的時候有沒有這樣一個目标,就是說我成立這個文學社,最後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狀态才是您想要的?
于:我們就是希望中文系,熱愛文學的人,寫詩的,寫散文的,寫小說的都可以,大家能夠團結起來,在一起玩,一起辦刊物,發表作品,大家在一起讨論,提高寫作的水平,這個是完全達到了。《銀杏》文學社組織了好多次會員集體登山、朗誦作品、郊遊,那真是一個非常好玩的時代。我們曾經去長蟲山,登上那個山的最高點。我記得那次去了十幾個人。中文系嘛,有很多男生女生喜歡文學,很多人都在做作家夢,這是很正常的。那個時候各個大學的這個文學社之間是有來往的,要寫信、要寄贈刊物。所以《銀杏》文學社逐漸在大學生裡面開始有了聯系和影響力,大學生都知道雲南大學有個《銀杏》文學社。那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文學社之一。
房:于老師請問您們當時是和哪些大學有交流呢?
于:重慶大學、好像還有西藏大學,那時候和北京的那些大學聯系不多。但是,他們也會寄他們的作品過來。比如海子,他就會把他自己印的詩集寄給我。那時候每個詩人都會自己印自己的作品集,因為你不能出版,就自己去油印一本自己的詩集,這就成為詩人的一個慣例。我也會印,每隔一段時間,我把我最近寫的作品打印出來,可能有30份左右寄出去給一些朋友,那個時候為什麼是西藏大學呢,因為那裡有一個文學刊物叫《拉薩河》,《拉薩河》的主編我記得他叫洋滔(原名楊從彪),他辦了一張報紙,上面就登全國各個地方大學生的作品,用那個報紙印得整整的四大闆。《銀杏》文學社就有三個社員的作品登在上面,大家就都知道這個《銀杏》文學社了。
鄧:您剛提到說創建文學社是一群好朋友、文學愛好者一起是嗎?那麼你們對于文學的想法和宗旨是否會有發生分歧的時候,那這個時候怎麼解決呢?
于:那個時候呢分歧不是很大。你看80級有我是吧,還有韓旭、吳丹,81級有社長朱紅東,然後還有副社長蔡毅,82級有文潤生,張稼文、錢映紫等,你們都應該知道。那麼為什麼我們分歧不大呢?是因為我比他們年長10歲左右,然後呢,我在文學上比較成熟,我在文學上的主張,比如用明白的話,寫日常生活,我會經常會講,他們也都有同感。那時候朦胧詩,就是北島、舒婷、顧城這些詩人在詩壇是走紅的,主流刊物都發表他們的作品,我們對此非常不以為然,在這一點上,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分歧也有,也不是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有的同學他更傾向于浪漫主義那種方式,我更主張用日常語言,胡适主張的言文一緻,用平常說話的這種語言、口氣,我不喜歡“口語”這個詞,我沒有說我的詩是口語詩,那是後來批評家加在我頭上的帽子。詩應該像朋友之間在聊天一樣,像朋友之間的談心,詩應該像這個桌子上的一個小筆記本,一副眼鏡,一個火柴盒,一個打火機,一個戒指,一個手表那樣的東西,不應該像朦胧詩那種隔着一層,高高在上的,必須要舞台上用普通話朗誦,專業演員朗誦的那種。我認為詩就應該像鹽巴一樣,像生活本身一樣,親切自然,讓人在瞬間,就是忽然你瞟一眼,唉,怎麼梨花開了,我現在才看見,那麼自然的一個東西。有的同學他也喜歡那種朦胧詩,但是我們沒有就此發生過的争執。

于堅:《詩六十首》,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圖片來源:朱興友提供)
鄧:文學社的社員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進入文學社呢?因為我們看到文學社裡面有一些經常參加活動的人,就比如說周良沛先生,他既不是雲大的學生,也不是您的同齡人。那他們都是以一種什麼方式進入到這個文學社的活動當中呢?
于:那些學生呢,他要跟文學社的這個副社長文潤生說一聲,說我想來加入這個文學社。另外呢,我們也要看過他的作品,他寫在信紙上拿來看一看,大家覺得還不錯就可以了。
鄧:所以加入文學社有兩個條件,一個是他自己得自願提出說我想要加入文學社,然後他要給大家看他的作品。
房:這是不是說明《銀杏》的影響力已經很大了,學校外面的人都知道并且想主動地加入它?
于:《銀杏》文學社的活動是開放的,所有的人都可以來玩。那麼有些人他隻是來玩,他不是《銀杏》文學社的,比如說周良沛,他是非常有名的一個老作家,他隻是來支持年輕人的。文學社為什麼這麼多人,相當于在那個時代成立了一個組織,那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所以呢,就不隻是學校裡的人,社會上的人也很關心這個文學社是不是有什麼活動。因為大家都渴望,有一個純粹的文學組織,可以找到一種存在感、歸屬感。我可以念我的詩,還可以和年輕一代談談我的文學上的看法,有很多老作家就會來跟我們談談,他對文學的想法,我們也會交流,因為來的不隻是周良沛,還有其他作家,我記不清了,但經常會和這些文學社的社員玩。後來做了社員證,一号社員證就是我的,很正式地發給你一個社員證,就是一個紅的,下面連印都沒有,隻有你的名字。但是拿一個社員的證件給女生看,她甚至可以嫁給你,你知道嗎?那個東西有居然那麼高的威信,得到那麼高的社會信任,是不得了的。
何:這和80年代是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是有關系的吧?
于:你想你是一個文學社的社員,這不得了這就等于是認可了你是一個詩人,一個作家,你知道這個有多了不起。我的社員證是第一号,那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專門印的《銀杏》的社員證,上面有一個銀杏葉,不是手繪,直接用一個葉子印出來的。
鄧:因為您已經提到了社員證,我就繼續往下問,我看到張稼文老師在《陽光燦爛》這本自傳小說裡面提到了,就是您畢業之後,他才成為那個社長,他就想去規範一下文學社的章程,做了社員證,所以您的社員證是您畢業以後他才給您做的,還是您在校的時候就已經拿到了?
于:應該是我畢業之後他們才做的,因為在我那個草創時期呢,就像剛剛上井岡山,那純粹就是好玩,大家在一起,文學青年在一起交流,就沒想到那麼多。張稼文他們那時候,系裡面也很重視,不像原來,後來還認為這是中文系的一張名片。你看,我們這個文學社可以培養作家,所以系裡面很支持。這已經和我那個時候冒着被發配到新疆去的危險完全不同了,系裡給經費了,要印刷什麼都很方便。刊物也豪華多了,會員證也是學校出錢給他們印。從張稼文開始它走向了體制化。之前,那完全是民間的,就和《犁》差不多,經常面臨着随時會被叫停的危險。後來就不會了,就等于是一種正式的形式,估計還有文件承認這個文學社是中文系的一個合法的組織。我那個時候,雖然不說出來,但它并不是完全合法的一個東西。
房:當時有沒有出現來幹擾你們平時文學活動的力量或其它事情呢?
于:那個倒沒有,因為我們那個活動就是純粹的文學活動。成立以後,其他老師都非常支持,我們一搞活動中文系的好多老師都會來。他們還會發言,老師是非常支持的,因為老師自己也想搞,那時候沒有這種事啊。大家都是從文革過來的,一直夢想着有一天能回到一個正常的文學時代,就是我在左拉的小說裡看見的那種,而這種時代終于到來了。像聶魯達這樣的詩人,他在大學裡面都是組織文學社的。你看今天你們讀的很多詩人,青年時代在大學裡,他都屬于一個文學社。這隻是夢想重新回到這麼一個文學的傳統裡,或者是建立一種世界文學的傳統,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你們也可以繼續思考。

于堅:《于堅詩集》(圖片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
鄧:我們了解到文學社的社員創作的最多的就是詩歌,那麼其他方面的創作成果怎麼樣呢?
于:都有啊,有一個叫楊林青,那個姑娘個子很高的,很漂亮,她的小說寫得太棒了,相當好,但她現在去美國了。還有韓旭,他的小說也是一流的,我認為是很成熟的小說。還有寫散文的,都有,而且并不少。寫散文比如申倩也寫得很好。《銀杏》文學社我認為是一個天才的文學社,很多人其實寫得很棒的,隻是因為沒有持續,就在大學裡面玩一玩,後來就沒寫了,其實那時候他們已經寫得很好了。比如朱紅東也寫得很好,寫長篇小說的劉建國也寫得很好。而且《銀杏》文學社它不隻是我們雲大的文學社,實際上它已經成為雲南高校的文學社的一個核心,比如說師大那個《野草》《紅燭》文學社,他們都過來一起玩。還有民族學院的《芳草》、醫學院的文學社。文學社每個大學都有,以雲大《銀杏》文學社為核心、領袖,有什麼活動都是我們召集起來,所以文學社的社員是一個很廣義的範圍。
鄧:這其實不能把社員的定義定在雲南大學的嗎?
于:這個還是要這麼看,正式的社員都是雲大的,但是來和我們在一起玩的不僅僅隻是雲大的,也不僅僅是中文系的,還有曆史系的,政治系的,物理系的,化學系的。很多學生喜歡搞文字的都會來,文學社等于像一個燈塔,把大學裡面的文學愛好者團結起來,照亮了那些黑暗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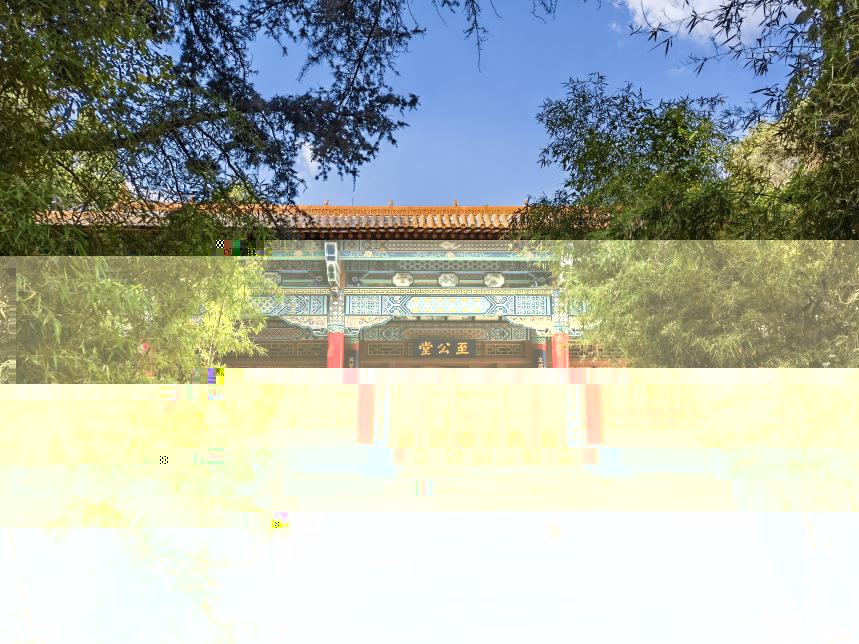
雲南大學東陸校區至公堂(圖片來源:王雲杉提供)
房:那這個排版呢?是您一個人來設計,說這上面要抄一些什麼,還是大家一起研究?
于:我這人太能幹,都是我幹的。因為那時候對文學簡直處于一種狂熱的狀态,你感覺到你自己已經成為巴黎索邦大學的一個前詩人,你馬上就會從這裡成為一個真正的詩人,充滿了激情的詩人。

雲南大學東陸校區鐘樓(圖片來源:王雲杉提供)
鄧:我們現在宣傳一些東西都需要申請,(學校)會(擔心)我們宣傳的内容會有一些不太好的東西。你們當時呢?
于:沒有,那就是我決定,我想發什麼就發什麼。但是,你要知道自由就在于——自由不在于不讓你做,而在于你知道你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雖然沒有人來審你,不會有老師來問你,你要貼什麼,我想貼什麼就貼什麼,那麼我也不會貼會被取締的那個東西。那個《犁》文學社它就不一樣,他們一開始進門的學生膽子太大了,開始是學校門口有那種大字報專欄,你們知道那種大紙嗎?他們直接把詩什麼的寫在這個上面,就有很多驚天動地的東西出來,那很快就被取締了。
房:那您自己辦的那個報紙還留着嗎?
于:我沒有那麼自戀。因為很多東西都要扔掉,留着幹什麼?因為沒有想到以後會是現在這個于堅是吧,我想的隻是這個時候。就像你們一樣,也許你的這個手機可以進博物館,因為是你用過的,你會因為這樣留着現在的這個手機嗎?那也太自戀了。
鄧:那您現在是會不會有遺憾呢?年輕時候寫的東西沒有保存起來?
于:這是一個宗教态度,知道吧?這些生命總是要煙消雲散,重要的是在那個瞬間,你是否體會了生命,你有這個感覺就可以了。我每天都要寫毛筆字,每天半小時左右,如果要賣的話,我可以賣幾千塊錢一個字,因為這個可以賣錢,我就留着這些字,那我不是個傻瓜。我每天寫的字,無論怎麼好,都是揉成一團扔垃圾桶裡。我見過寺院裡的僧侶做壇城,用彩沙做,有時候畫出一個要三個月,已完成,用手一合,成為一堆沙,抖到河裡去,他完成的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要有這個勇氣,小姑娘,忘記了就忘了,一個生命就是一塊土地,它永遠會有糧食生長出來,隻要你澆水,你的天空下永遠有雨水澆在你的土地上,那麼靈感自然會生長。我是有些手稿,隻是放在那裡而已。
房:您在寫這些手抄報、宣傳報的時候會不會每一期都想要傳達一個自己對詩歌、文學的理念?
于:不會有,比說這一期我要有一個主題是吧,紀念五一是吧?國慶節專刊是吧?(衆笑)我唯一的标準就是這個東西寫的好,這首詩發出去,它不會讓人家覺得這個主編是個弱智,他隻是因為有這個權利,所以他才來幹這個事。它發出去,我想象中的讀者的标準,那應該看了這些作品就覺得,這個文學社我應該去參加。你們也要這樣做,因為這個時代的人太迷戀權力了,有些《銀杏》文學社同學來采訪,跟我說這個是什麼頭銜,那個是什麼頭銜,亂七八糟,理事,秘書長,那太可怕了,你們是要成為詩人作家的人哪。用體制那一套來要求文學,文學的本質就是反體制的,為什麼我們需要文學?就是文學表達的是和體制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體制不是政治的意思,體制要求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規劃好,文學就是要把這個搞亂。體制要求的就是确定,一切都要确定答案,就像數學,一道題隻有一個答案,文學隻有一個答案,是不是很可怕?文學本來就是要表現世界、人生的本來的不确定。
鄧:我們發現其實您在銀杏文學社的時候,成員當中也粗略地劃分了職位,就比如說每一屆有一個社長,一個副社長,然後有一個主編,您覺得社長副社長和主編他們的職責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于:我這個主編呢,主要就是負責刊物的質量。社長、副社長他們主要是去召集會員的活動,要把這個編好刊物拿去付印,他們幹這件事。召集活動是主要的,那時候誰也沒有錢,比如說你還要收一點活動費什麼的。有一天晚上,我們一夥文學社的,喝完酒就順着那個盤龍江走,穿過那個桉樹林的小路,在黑暗裡面一直走,一路上聊天喝酒,走了一夜,天亮的時候,大家餓得要死,所有人身上加起來隻有5分錢,隻有一個人的包裡面有5分錢,5分錢可以買一個燒餌塊,我們6個人一起分,這就是銀杏文學社。我們和安東尼奧尼電影《紅黑藍》裡面拍的是一樣的。大家在一起就是讨論文學、人生,什麼是最好的,要怎麼寫。我們那時候讀了西方的東西,講得最多的,比如說存在主義啊,薩特《等待戈多》《秃頭歌女》還有那些最好的詩人的詩,背誦普希金的《緻大海》,聶魯達的《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的歌》,希臘詩人埃利蒂斯的《瘋狂的石榴樹》,那是張口就來,詩集都是放在包裡面随時拿出來打開。自己能寫出這種詩嗎?随時在想,每天都迷狂在這種文學的氛圍裡。
鄧:我們現在就沒有這種感覺了。
于:你們被教育摧毀了,這個教育把你們改造成機器人,你沒辦法。但你們可以自己反抗,你看你們現在坐在這裡和我聊天,就是從機器裡面走出來。回到純情少女,天真、好奇,讓過去黑暗裡面的生命充滿火光、激情,就很好嘛!
鄧:您是否還記得您在校期間最後一次文學社的活動?想問一下您那時候是什麼心情?
于:有兩次重要的吧。我的詩在《飛天》獲獎,甘肅的《飛天》有一個偉大的編輯張書紳,他開辟了一個“大學生詩苑”,那時候大學生沒地方發表作品,一般的刊物是不會發大學生作品的,《飛天》開設了“大學生詩苑”,全國很多大學生都往那裡投稿,在甘肅蘭州辦的。我們文學社也有幾個社員,比如朱紅東就在上面發表了詩歌。我的詩一寄過去他就非常喜歡,我幾乎都是發頭條。兩年後《飛天》頒發了“大學生詩苑”詩歌獎,第一屆就頒發給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獲文學獎,寄的獎金是50塊,這不得了。我把50塊獎金拿來請文學社的全體社員,加上一些其他朋友,可能有20多個人,去華山西路的一個老飯店裡面全部吃完。另外一個就是最後一次是我們一起去西山頂,頭天下午出發,穿過山崗、荊棘叢和岩石,找到一個地方在那裡睡了一夜,一直就到天亮起來,站在西山頂上看日出,日出之後我們才回去,這是印象最深的,最後一次。那時候社員已經很多了,還有些是幹部進修班的,他們也跑來參加。
鄧:文潤生老師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到您畢業之後,經常參加社團舉辦的“紅五月”詩歌朗誦活動,這個活動它是跟其他的高校一起聯合舉辦的,在會上朗誦詩歌,您還記得您堅持參加了多少屆嗎?
于:這個不記得了。我雖然已經畢業了,但每天上完班就往學校裡面跑,東二院宿舍,中文系的學生都住在那裡,我們經常在宿舍裡面聊天,至少持續了兩年。幾乎所有的文學活動我都會去參加,為什麼不去呢?這太奇怪了是吧?好玩嘛對不對?就像你每天要去食堂打飯吃,就那麼簡單的一件事,你為什麼會不去呢?
鄧:當時雲大它也有很多其他的社團是非常出名的,比如說雲南大學的演講協會,還有雲南大學武術協會,您除了參加文學社還參加了别的社團嗎?
于:沒有沒有,那時候社團之間是不聯系的,各玩各的。因為這個社團它是一種同人社團,它有點像30年代魯迅他們那種文學社團的性質,同人在一起搞這種活動。它不是一個學生校園活動這種概念,它就是一種同人的,大家對文學有興趣,見解差不多,大家就在一起玩。不會說其他的社團的活動我們也去嘗試。我都不知道你說的這些社團。他們也是一樣,他們也不會來找我們玩。
鄧:那其實和現在的大學生社團不一樣。
于:完全不一樣,因為這個已經成了學校體制的一部分,我們那時候完全是古典的、傳統的文學社,就和四十年代西南聯大的那種文學社團是一樣的,是那種概念,不是現在這種。
鄧:我們了解到您現在也有專注于就是攝影愛好活動。
于:不是攝影愛好。我是攝影家。那時我就開始攝影了。我父親給我的獎勵就是送我一個照相機(海鷗205)。我在70年代就喜歡攝影,我是借來的相機。看吧(指向書店牆壁上的照片)我的作品就挂在那,我是一個專業的攝影家,隻是我不想在這方面有什麼讓人家知道的事情,自己玩就好了,我們那時候拍膠片,拍完之後自己沖洗,這一套我都會。
房:那您會幫社員們拍照嗎?
于:偶爾,拍過幾次。可能還有幾張吧,有集體照。網絡上都搜得到。
李:設置文學社的時候您會把“攝影”這一模塊也放進去嗎?

于堅自選集(圖片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s?)
鄧:那您現在會看90後,甚至00後寫的東西嗎?
于:會啊。我的微信上很多90後的朋友,他們會把作品發給我,讓我看看,像你們一樣的小姑娘小夥子都有。
鄧:那您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和您這一代人寫的詩有什麼不一樣嗎?
于:沒有“你們這一代人”這種概念,隻有天才和蠢材。在任何時代隻有這兩種人,就是寫得好的和寫得不好的。和這個“代”沒有關系,任何時代,任何一種人他都會産生真正天才的好詩人,90後也有很多我認為寫得很好的,但也有大量的庸才。
何:老師請問現在他們的詩歌裡面有沒有一些表達的方式,或者說是描寫的一些東西,是你那個時候感覺不太會有的,就是給人一種比較新鮮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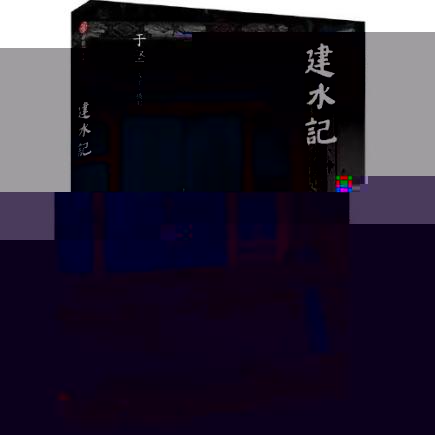
于堅:《建水記》(圖片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
于:那肯定有,因為現在的這一代人他們看的書相當豐富,不像我們那時候那麼封閉。他們寫的時候出手不凡,一看就非常像詩,就是一般概念裡面詩就是如此的那種。我當過很多大學生詩歌比賽的評委,我還是複旦大學光華詩歌獎的主席,我6月份要去上海。但是有一個很不好的地方,大家的詩都是太像詩了,沒有感覺。這個小夥子太漂亮了,非常标準,長得就像周傑倫,但是沒有感覺,這個太可怕。感覺那個東西就是我說的天才,你要感覺得到生活中的詩意,很平常的東西經過你的筆一寫那種感覺就出來了。感覺到底是什麼?那拿詩來看,我說不出來。離開詩這個東西就不存在,它不能概念化,這首詩拿走這個東西就不見了。年輕一代,我認為可能是父母、學校的長期教育,不鼓勵生命的開放,而是規範你,最後你就非常緊張,你寫詩也是,認為詩就是一個和你的内心沒有關系的,完全就是你的語文很好、造句造得很好,但詩是一種生命的解放,你本來在這種人生裡面很無聊,通過詩你會發現生命還有另外一種過法,你看艾略特的詩,看狄金森,看艾倫·金斯堡的詩,你發現生命還可以那樣去湧動。詩就有這種魅力,你可以今天看完這首詩,明天就上路,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到這一點。
鄧:《銀杏》文學社還一直在發展着,但是它的發展存在一些問題,一些阻礙,比如說它的成員現在招進來,大部分都是文學院的學生,很少有數學學院,物理學院,化學學院的愛好者加入進來,可能文學愛好者在變少,這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剛剛樂思說到的,現在文學社舉辦一些活動,其實都是靠學院承諾給獎金和獎項這些,所以大家才會來參加活動,自主性在下降,您怎樣看待這些現象?
于:這個是學校的教育理念出了問題。文學是一種語言的解放,它是一種自由,你可能在任何方面你都是被規範的,你是被束縛的,但是你通過語言,你的生命可以獲得解放。比方說你完全可以在日記裡面寫你想寫的任何事,你不發表不就完了,因為這個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它可以不涉及他人,這純粹是你的自我發現。如果這個教育理念不改變,教育不是把人的生命打開,讓他意識到他自己到底是誰,隻是用一個标準來規範,把每一個人都按标準培養,考試通過了就畢業。為什麼今天大學生裡面有那麼多會抑郁的人,我那個時候沒有一個抑郁症。《銀杏》文學社是一個沒有抑郁症的文學社。
鄧:那您對于現在社團的進一步發展有什麼建議嗎?
于:我覺得同學應該多讀書,讀書是什麼?讀書是要知道好歹。你通過閱讀你能知道什麼是好的東西,什麼是真正的文學,什麼是僞文學。因為我發現現在年輕一代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好歹,不知好歹是這個手機造成的,任何垃圾隻要排了版,配個圖片在手機上出現,你都會有一種神聖感,你都被動地接受,完全喪失了判斷力。我覺得要通過閱讀,為自己建立一個文學史,什麼是你真正喜歡的、好的,使你的生命經驗被被喚醒的。你要建立一個自己的閱讀,然後才談得上其他。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學生好壞都不知道,最好的東西,最差的東西,他寫論文的時候都是用同樣的語言。卡夫卡的小說,曹雪芹的小說,李白的詩和張三李四王麻子的都是一套語言,太可怕了。要知道什麼是好的,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銀杏文學社,包括現在師大我的這些研究生,我是要教他們什麼是真正好的東西,它好在哪裡,慢慢他就會形成一個标準,他就不會盲目地跟着手機跑,什麼烏七八糟的東西喬裝打扮一遍,巧言令色,都是害人的東西,結果小孩因為沒有判斷力,認為隻要發表了、站在台上了、隻要獲獎了,那就是好的,這種标準太可怕。所以你經常看見那種你完全無動于衷,讓人昏昏欲睡的東西在獲獎。
鄧:最後一個問題,您對現在的《銀杏》文學社的那些人有什麼期待,或者說您想對現在堅持創作的人說些什麼?
于:現在呢,《銀杏》文學社已經進入了體制,在這個體制的保證下它要辦下去,我覺
得沒什麼問題。我隻想請社員,好好地回到我們成立文學社的那個地方,去老校區認真地看看銀杏樹,看看每一片葉子到底是什麼顔色,它是怎麼生長的。好好想一想。銀杏是來自大地的樹葉,它不是一個圖書館書齋裡面的東西,它是會變化的。它在春天會像小鳥一樣長滿了綠色的翅膀,然後它慢慢地到秋天,它變得像黃金一樣,我很多詩寫到《銀杏》文學社,到冬天它獨立寒秋。放下書本好好想一想銀杏樹到底是一種什麼樹,别的不要做。
鄧:今天非常感謝于堅老師接受我們的采訪。
于:這個小姑娘太正式了,像開會一樣。
鄧:沒有沒有,其實我們大家都挺緊張的,給您發消息的時候我也是挺忐忑,不知道您是否有時間。
于:不會的。我這個人做事呢,我說了要做的事我就要做,如果我沒說呢就是我還沒決定,好事你總要等待嘛,微信時代,你剛剛一秒鐘發一個消息,你就希望人家下一秒就要回你。你很有耐心,我很高興,過了兩周三周我給你發信,你還是這樣期待的,那麼我覺得這個同學可以見一見。三個星期過去,她如果覺得于老師架子太大了,這真是個名人。我們過去一封信要一年才收到,你怎麼辦呢?一封信寫出去兩個月三個月才能收到,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今天什麼事情都是“短平快”,你們要學會慢慢地生活,要慢下來。《銀杏》文學社的人,如果連銀杏樹是什麼樣子,它在冬天是什麼樣子,它在秋天是什麼樣子,你仔細看,不是小資産階級文學所寫的,一個金色的黃昏一樣的東西那麼簡單,你仔細去看,每個人都可以寫出完全不同的感覺,那是細節。那今天就這樣。
衆:謝謝于堅老師,于老師再見。

同學們與于堅老師的合影(圖片來源:鄧萦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