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探索世界的方法
——錢映紫訪談錄
受訪人:錢映紫
采訪人:畢曉蕾、鄧萦夢、何子怡
采訪時間:2021年12月6日
采訪方式:電子郵箱
采訪者:請問您當時是怎麼加入銀杏文學社的呢?您加入文學社的初衷是什麼?
錢:很簡單,當時想着有個社團大家可以一起玩,就參加了。
采訪者:當時文學社也經常會有校外的人員來參與活動,例如周良沛先生,這些校外人士是如何得知銀杏文學社的活動信息的?校外人員入社的情況多嗎?是不是說當時文學社的影響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
錢:不知道,應該有專人負責通知邀請,當時也沒有電話,通常是通過寫信或者上門邀請。那時的作家大多很謙和,也容易邀請到。校外人員入社是後來的事了,我不清楚。社外同學大概就覺得文學社是個圈子活動,一些有寫作才華和寫作熱情的文學小圈子吧。
采訪者:當時和您一起加入文學社的這些女生中,您對誰的創作印象最深?您能和我們講一講女社員們在文學社的創作嗎?比如說誰最擅長哪一種文體的寫作?給您印象最深的作品是什麼?
錢:第一批加入文學社的就我們82級女生最多,比較活躍好玩。至于寫作,懵懂得很,也就是玩玩詞句語感,模仿一些自己喜歡的文字。印象深的是女同學楊黎堅的一首詩,大意是:媽媽想戀愛了,父親就出現在她面前;當她想成為母親,我就來到了她的身邊。如今,媽媽問我在想什麼,我說什麼也不想。就這首短詩印象最深,大緻意思是這樣吧,詩句不一定準确。當時覺得把愛情與生命的某種宿命性寫得自然而又神秘。大多數女生的寫作都單純,在今天的語境來看是很幼稚的。但那時,已經突破了語文課本的寫作範式,這種寫作帶來的解放感,隻有我們這些在文革後期背着領袖語錄成長起來的人才能體會。
采訪者:當時這些女社員是如何評價男社員的創作的呢?大家最欣賞哪幾位男生的創作?
錢:那時女生喜歡的有文潤生同學的詩,樸實美好的愛情詩與鄉土情懷。還有于堅,我們覺得他樣子作派都有種海明威的硬漢氣質,詩歌寫得陽剛氣十足,不過讀的也不多,他不怎麼跟我們讨論詩歌,可能覺得我們太幼稚,嘻嘻。其他如張稼文的散文詩,有點美有點晦澀。蔡毅那種充滿排比的馬雅可夫斯基式的詩歌,朗讀起來有氣勢,還有韓旭、姜大才,寫作都相當有才氣。
采訪者:您身邊有沒有不是銀杏文學社社員的同學,比如您的室友,她們這些社外人員當時是怎麼看待文學社的?
錢:不參加文學社的也多,我們一個宿舍差不多一半多沒參加文學社,她們不是不愛文學,而是對寫作這件事興趣不大而已,隻是不參加文學社的讨論活動,遇到文學社搞詩歌朗誦會會後還有舞會什麼的,大家都一起來玩,唱唱跳跳,舞會很熱鬧。
采訪者:當時大家會不會借着文學之名,開展一些聯誼活動?您能和我們講一講那個年代你們的交際生活嗎?在您看來這是一個怎樣的年代?
錢:借文學之名搞聯誼活動很多,朗誦會、戶外活動、舞會什麼的,比上課更有吸引力,我猜很多人參加文學社就是為了玩,男女生互相認識,借機交往。當時社交活動比較單純,男生女生在一起學喝酒抽煙,一群人在宿舍徹夜空談人生、價值、美、愛情、崇高……在各個大學舉辦舞會,彈吉他唱歌等等。有一次,幾個不太熟悉的低年級男生抱着吉他跟我們幾個女生搭讪成功,一起在足球場彈唱到深夜,回不了宿舍,索性唱下去,會唱的歌都唱完,後來唱不動了,淩晨寒氣逼人,在球場到處找廢紙、樹枝燒來取暖,直到早上宿舍樓大門開了才疲憊倒床。那時的交往主要是為了好玩愉悅,有時也會暗自期待遇到一個喜歡的異性。不過,對于當時我們這些女生,那個會帶來愛情的人非常抽象,大多不會是身邊那些胡子和體味都很具體的男生。
采訪者:我們在整理銀杏文學社資料的時候了解到,當時您們在東二院宿舍裡面開了一個咖啡館,作為“銀杏文學沙龍”,您能給我們描述一下當時是怎樣一個“盛況”嗎?
錢:學生們小商小販做生意,不再恥于談錢,就像是一種行為藝術,印象中隻是熱了一頭子,大家都想賺點錢。文學社也想給自己賺點活動經費用于油印刊物什麼的,相當于勤工儉學,大家都是義務。東二院宿舍一樓拐角大約二三十平米的空間,就着學校沒用的桌椅,稍微裝飾了一下牆面,一個大保溫桶,幾把五磅八磅保溫壺,不多的幾個杯子,用開水沖點速溶咖啡、奶粉、果珍,外加炒瓜子、奶油花生一類的零食。吸引來一些時髦男生,他們會帶女生來喝點沖泡牛奶呀買包花生呀坐着小聲說話。在那裡見過詩人周良沛、作家張長、曉劍、嚴婷婷,他們都自己掏錢買飲品,還很有耐心跟學生們談文學。這個文學沙龍不記得堅持了多長時間,就收場了。一種嘗試,諸多禁忌打開後,做以前不被允許的事,算是初嘗自由的味道。
采訪者:之前我們采訪于堅老師時,他說到當時文學社還會和西藏、重慶的一些高校有交流活動,您當時有參與過這些交流活動嗎?(當時大家都通過什麼方式交流?)您還記得具體有哪些高校嗎?
錢:文學社活動我後期參加得少了,也沒有參加過跟省外文學社的集體交流活動。除了讨論會,那時的很多文學交流都是寫信。我後來也曾經跟友人寫信交流一些文學與讀書話題。
采訪者:請問當時社員們的作品發表在哪些刊物?如果有人發表了作品,那麼文學社裡會組織什麼樣的慶祝活動?
錢:作品能變成鉛字、印刷品,就算是很大的成功。當時知道的隻有《蜜蜂報》《醜小鴨》《飛天》《山花》,能上《詩刊》是最牛的吧。有人發表作品大家都很開心,稿費請大家去館子吃喝,花完!
采訪者:當時文學社的成員都有一個社員證,您知道社員證的設計理念嗎?之前我們采訪于堅老師和張稼文老師的時候,他們說很多人的社員證當時都被拿去換酒換肉了或者是已經找不到了,張稼文老師目前聽說就隻有您的社員證還保存着,您能借我們看一看嗎?
錢:最早的銀杏文學社員證很簡樸,不清楚有什麼設計理念。我的還在,回頭可以把照片發給你們看看。

銀杏文學社社員證(圖片來源:錢映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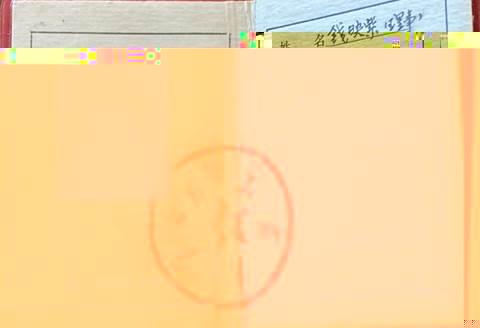
雲南大學銀杏文學社社員證(圖片來源:錢映紫提供)
采訪者:當時社裡有很多大理老鄉,像文潤生老師、朱紅東老師他們都是從大理來的,您畢業以後回到大理也和他們成立了“風”文學社,您也寫過《龍關上下——沿着下關的地名》這樣的文章,請問您是怎麼看待您的故鄉對于您創作的影響?請問您認為當時“風”文學社和“銀杏”文學社最大的區别是什麼?可以說“風”是“銀杏”的延續嗎?還是說二者之間在精神内涵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錢:《風》是大理文學愛好者搞的油印文學刊物,參與策劃編輯出品散發工作的多是前文學社成員,不僅僅是銀杏社,還有民院野草社的。《風》跟銀杏社沒有什麼關系,不是一個有章程的文學社團,就是一群有寫作熱情,價值觀、文學态度相似的人,出校工作後不甘平庸,想通過寫作堅持理想與心性,我們把作品集中發表交流,并成為生活中的好友,經常在一起的就十來個人,一起登山一起喝酒唱歌一起歡笑流淚,幾十年彼此信任肝膽相照,終身好友。《風》跟銀杏社非常不同,銀杏社是一個有章程的有目的社團,而《風》是随心而往的同仁,組織更松散,感情與精神聯系更親密,幾十年後回首,覺得頗有“古風”。大理對我的影響,應該是塑造,山水自然傍着古老曆史,風流雲散而山川依舊,人是渺小的,生是短暫的,看看山水流雲,人會平靜下來,所謂冥想之城。
采訪者:之前采訪張稼文老師的時候,他說當時您的散文寫得最好,您畢業以後也在堅持着散文寫作,請問您認為畢業以後的寫作與校園期間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是什麼原因讓您的創作産生了變化?
錢:得大家厚愛,但我不覺得自己寫的有多好。在校寫作,人生經驗有限,寫作也是延續着中學作文體,難脫幼稚與矯飾。工作後任務性的文章寫的多,故個人寫作隻追求小的、具體的、及物的、出脫于宏大話語和目标的,一物一說,自娛自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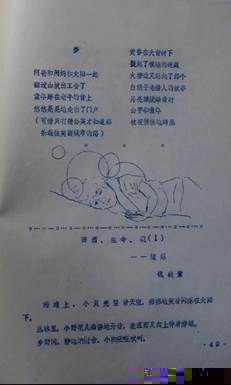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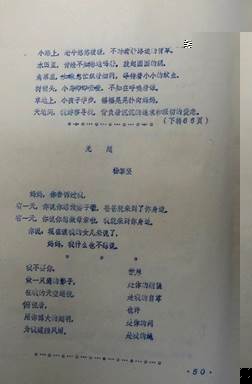
1985年錢映紫詩歌《田園·生命·我》發表于銀杏刊物(圖片來源:錢映紫提供)
采訪者:您覺得加入銀杏文學社對您人生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錢:銀杏社對我沒有什麼大影響,但是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人生記憶,沒有這些記憶,回看自己的生命,就會少了幾分意思。
采訪者:您滿意現在的生活狀态嗎?能說說當時和您一起的銀杏人現在的生活狀态嗎?大家還在創作嗎?
錢:對人生是否滿意,跟文學好像沒什麼關系,愛不愛文學,當不當作家,都得承擔生而為人的責任,區别在于勞作之後,能否感到更多的“詩意栖居”———人生的精神意味。當年的文學愛好者成為專業作家的少之又少,我們大多數人不過普通人而已,做個正正常常的普通人,也沒什麼不好。
采訪者:您想對現在仍在堅持創作的“銀杏人”說些什麼呢?
錢:真誠寫作是一種精神冒險與開拓,年輕時候的這種探索對一生的精神成長非常有益,所以,喜歡就真誠寫用心寫,不要急于求成,很多年後你會發現,這種探索活動會讓你看世界有更大的維度。

錢映紫在登山途中(圖片來源:錢映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