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潤生訪談錄
受訪者:文潤生
采訪人:鄧萦夢、畢曉蕾、何子怡
整理人:鄧萦夢
時間:2021年6月15日
形式:郵件采訪
采訪者:您作為銀杏文學社的第二任主編,當時您們刊物選取作品是什麼樣的标準呢?您能和我們講一講《銀杏》從最初選作到最終刊印的過程嗎?
文:好像也沒有固定的标準,一般都是憑直覺選稿,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大學生都有很好的審美素養,大家都看了很多文學的大部頭和文學期刊,具有欣賞文學作品獨到的眼力,能夠有勇氣把自己手寫的文字拿出來給大家欣賞,應該是自我感覺不錯。而且社刊都是發表本社社員和已經畢業的老社友的作品,篩選起來相對就容易得多。
采訪者:第二個問題緊跟第一個問題,也是關于《銀杏》文學雜志的。據了解,銀杏文學社在第一任主編于堅手裡還沒有紙質的刊物出版,是以壁報的形式呈現社員作品的。而在您和張稼文老師的努力下,銀杏文學社終于擁有了自己的刊物《銀杏》。您能講一講這其中的故事嗎?(例如:何時産生想有紙質刊物的想法的?刊物的經費哪裡來?如何與印刷廠溝通并敲定合作事項?根據什麼标準來确定刊物印刷多少冊?)

《銀杏》會刊1985年第6期(圖片來源:陳勇強提供)
文:我進入大一時就看過一本在中文系學生中流轉的油印刊物《犁》,其中有78級中文系李勃、費嘉、80級于堅等一幹師兄師姐的作品。我一就看愛不釋手卻不能擁有。于堅、韓旭等師兄發起成立銀杏文學社之初可能也打算要辦油印期刊,苦于沒有經費,所以就辦成了手抄的壁報,大部分作品都是主編于堅、副主編蔡毅等手抄的,那個年代壁報也很流行,我們的《銀杏》壁報張貼在在雲大本部人人必經的十字路口,上下課時圍觀的人很多,人頭攢動,産生了很好的影響,遺憾的是作品不能長期保存和流傳。後來文學社影響越來越大,在中文系主任張文勳、雲南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史宗龍等老師的支持下,《銀杏》才辦成了油印期刊。再後來雲南大學學生會成立了社團部,銀杏文學社發展成了全校性的文學社團,校學生會有打印機,我們的刊物就是在校學生會打印完成的。打印的過程我幾乎都有參與,作品都是手寫的,負責打字的是理科生,遇到字迹潦草的隻有幹瞪眼,因此刊物校對工作量也很大。在那個會打字的理科生退出後,我們隻好把作品拿到昆明的街頭油印部去打印。因年代久遠,當年每期具體打印多少本我都記不得啦。
采訪者:您們當時文學社的活動經費來源是什麼?學校支持和社員繳納社費嗎?您們有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來支持您們來維持銀杏文學社日常活動和其他朗誦、聚會等活動?
文:文學社成立之初取得了中文系主任張文勳、李叢中、喬傳藻等老師的支持,經常邀請全國全省的文學大咖如曾卓、白桦等來文學社開講座。後來發展成為全校範圍的文學社團後,校團委、校學生會提供了設備,油印刊物打印更加方便,有一段時期還提供了活動場地,在雲大東二院2棟學生宿舍1樓開辦了銀杏文學沙龍,經常有省内的作家詩人光臨。在校黨委宣傳部部長史宗龍老師的支持下,我們在東二院學生食堂樓上舉辦過“紅五月”詩歌朗誦會,參加者很多,場面蔚為壯觀。當然平時的交流活動大部分是在學生宿舍進行的,于堅、韓旭畢業後經常光顧我的宿舍,那時候于堅已經出名,大家都愛和于堅聊天,他仿佛有磁鐵般的引力,牢牢的吸引着年輕的缪斯“信衆”。八十年代中後期,于堅的詩句“像上帝一樣思考,像凡人一樣生活”幾乎成為雲南一代人的流行語。

張文勳先生(圖片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ct=201326592&z=&tn=baiduimage&ipn=r&word)
采訪者:當時社裡的女生也很活躍,像錢映紫、楊黎堅她們,都是文學社裡的活躍分子,請您能說說這些女生的創作情況嗎(可舉例)?當時社裡的這些小夥子是怎樣評價這群姑娘的?

左起:數學系的楊恒芬、梁蓓與中文系的金燕、趙白帆 (圖片來源:熊偉提供)
文:中文系82級有40多位女生,個個貌美如花,82級文學社積極分子有楊林青、陳麗媛、王英、錢映紫、楊黎堅等,83、84、85級有潘燕、彭彬、仇雪琴、徐玉玲等,理科系有好幾個女生相當有文采,名字記不得了。我知道有的女生偷偷的在筆記本上信簽紙上寫詩或散文,大多屬于情窦初開抒發感懷的那種,一些文字是在我死皮賴臉的央求下拿出來發表的。有的女生個性比較張揚如楊林青,她愛喝酒跳舞,每次文學社大型活動都少不了她曼舞一曲,大學畢業若幹年後去了美國。
采訪者:您大學畢業以後回到大理加入“風”文學社,請問您認為當時“風”文學社和“銀杏”文學社最大的區别是什麼?可以說“風”是“銀杏”的延續嗎?還是說二者之間在精神内涵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文:“風”在我畢業前就存在了,為首的叫呂二榮,曲靖人,雲工建築系畢業生,筆名林夏,分在大理工作,是我們銀杏文學社首任社長朱紅東的朋友。後來朱紅東、我、錢映紫、郭文平,還有民院的李桂根、張鴻光等等這些大學時就很熟的文學青年先後分回到了大理。工作之餘,大家就成天混在一起玩了。于堅也經常從昆明來大理跟“風”們在一起瘋,這些時光多次在于堅的文字中呈現。“風”是永遠的朋友圈,文學讓我們相識相知,而文學隻是這個朋友圈很小的一部分,共同的價值觀和品味讓我們這群人一輩子惺惺相惜,時常相聚直到終老。
采訪者:您的筆名“朵美”,是您故鄉的名字,想必故鄉對您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請問您怎樣看待您的故鄉對您創作的影響?
文:我十四歲上高中前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出生的村莊朵美,它在金沙江大峽谷中,一年四季天氣幹涸炎熱,家門口就是大江大河。大學時代我取過幾個筆名金沙、金沙子、朵美,于堅說還是朵美好聽于是就沿用了下來,作家姚霏(滄浪客)散文《大理小文》寫過我筆名的來曆,大約就是他說的那個意思。故鄉是靈魂的存在,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深入到骨髓中,那時遠離家鄉交通不便,思念父母,寫的文字自然少不了老家熟悉的事物。

金沙江大峽谷(圖片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ct=201326592&tn=baiduimage&word)
采訪者:很多銀杏文學社的成員大學畢業以後都很少甚至是不再創作了,隻有像于堅這樣的少數人在從事着和文學相關的工作,您是怎麼看待這一現實問題的?
文:大浪淘沙吧,淘剩下的才是精華。銀杏文學社前前後後有那麼多社友,成為作家大家的沒有幾個。這是體制的原因,很多中文系大學生到了體制内,人生的大部分時光都用在抄寫公文上,久而久之創作純文學卻手生了,手笨了,文學詩歌成了遙遠的記憶。當年有老師說中文系主要不是培養作家的,事實證明就是這樣。當然有文學社和中文系培養的紮實功底,我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寫作公文也應該是最棒的。
采訪者:我們從蔡毅老師處得到了部分1985年《銀杏》合刊的資料,您擔任主編,而副主編叫潘燕,這位成員我們了解不多,您能講講她(他)嗎?或者是否能回憶起你們作為主編和副主編工作側重點和配合方面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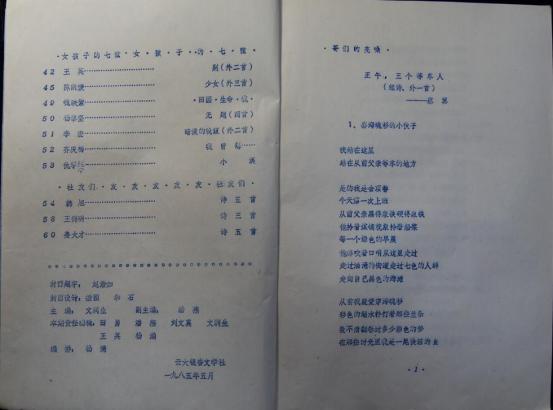
《銀杏》會刊,1985年5月出版(圖片來源:文潤生提供)
文:那時候文學社班子是這樣搭配的,高一級的擔任社長、主編,低一級的分别擔任副社長、副主編,也是為了交棒傳班下去。社長主要負責社務活動,主編主要負責編務。潘燕是中文系83級的,喜歡寫小說散文,是文學社活動的積極分子,于是就選她當了副主編,但是她在編輯方面基本沒有履職過,所以後來《銀杏》期刊就沒有出現過她“副主編”大名了。潘燕大學還沒有畢業就與于堅戀愛上了,後來成了于堅的妻子,在雲南出版社工作至退休。
采訪者:我們現在能從圖片中看到,刊物的作品中時常會插入一些很有創意的畫作,請問這些畫作都是銀杏社的成員自己畫的嗎?還是有邀請設計藝術系的同學參與制作?因為我們從第六任社長朱興友處得知,他在任時刊物的插畫是由美術系的非文學社成員的同學創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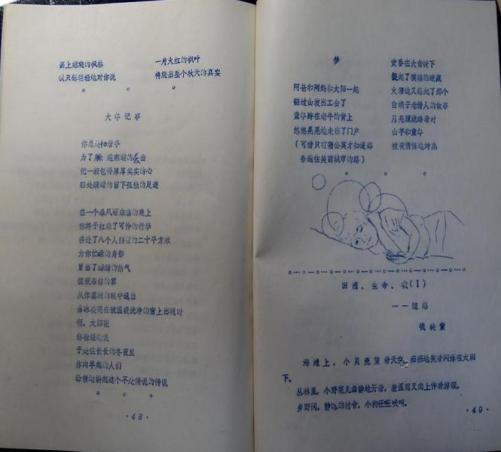
《銀杏》會刊(圖片來源:文潤生提供)
文:是文學社社友中有會畫畫的做了插圖,有的期插圖多,有的插圖少,每期的情況不一樣。
采訪者:我們看到1985年合印的這一本《銀杏》中欄目與欄目的分界線完全是由重複構成的,非常有趣味性,這和朱興友老師提供的後期雜志的欄目定名(一般是從該欄目下取一篇的名字定名)很不一樣。這個欄目的定名是主編自己決定嗎?那您還記得當時這期《銀杏》欄目這樣定名的原因嗎?
文:是當時這期《銀杏》欄目這樣定名的,“哥們的亮嗓”是81級就要畢業走向社會的五位男生的專輯,“銀杏樹下”則是82級和82級以下的男生專輯,“女孩子的七弦”顧名思義就是女生專輯了,“社友們”則是80級已經畢業的師兄作品。每期都會根據社員和作品的變化情況起名。
采訪者:據了解您畢業之後就去了大理電視台工作,因為您們當時的工作基本上是分配制,您在可選範圍内為什麼選擇了進入電視行業?您認為文學社的經曆會對電視台的工作産生何種影響?
文:八十年代中文系愛好寫作的畢業生夢寐以求的願望就是分配到文學社刊工作,以把自己的文字變成鉛字為榮。畢業前夕省文聯《大西南文學》(《邊疆文學》)召集了82級8位愛好寫作的同學到編輯部進行了書面考試,寫一篇外國短篇小說觀後感,經過評議後編輯部最終确定并向學校發函要我,于堅特地交代我去把長發剪短并領着我拜見了編輯部的各位前輩,待到畢業分配時卻是另外一個沒有參與考試的男同學被分到了省文聯,我則分回到了大理。好在大理州廣播電視局也派人到學校考察大理籍中文系畢業班學生,校黨委宣傳部長史宗龍老師特别推薦了我,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大理電視台工作,成了大理電視台最早的具有大學文憑的文字編輯和記者。每天與高大上的時政新聞打交道,但是詩歌文學情未了,1990年我開辦了一個大型電視雜志欄目叫《大理風》,其中設了一個闆塊“詩苑散步”,把詩友的詩作演繹成MTV一樣的作品,這在當時在全國來說還是不多見的,我還與大理州文聯合作舉辦了大理州首屆電視詩歌大獎賽,直到前些年與詩人潘洗塵合作舉辦“天問詩歌節作品朗誦會暨頒獎典禮”,把全國各地知名的詩人請到大理電視台演播廳與大理本土播音員主持人一起登台朗誦詩歌。
采訪者:銀杏文學社來自大理的成員還是非常多的,像錢映紫老師、朱紅東老師、郭文平老師等,在文學社内部是否存在同鄉創作互相影響的情況?您們的關系可以理解為是既相互促進又相互競争(競争是指在文學創作上互相激勵、“攀比”)嗎?
文:我們後來成了終生的朋友,可是除了錢映紫以外大家都很少涉獵文學了。
采訪者:您是第二任主編,您當上主編是于堅老師直接任命的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他選擇您?您認為你們那一撥人中,您的獨特之處或者優勢是什麼?
文:應該是是于堅、朱紅東、韓旭他們幾個共同确定的。我在高中時期就愛好文學寫作,在母校鶴慶一中讀書時擔任“鶴中青年”壁報主編,有編刊物的基礎。我來自鄉村,天性老實随和,與大家相處得來,這也許是他們選擇我當主編的原因。
采訪者:郭文平老師和您一樣進入大理電視台工作了,在工作上你們是好兄弟好幫手。那麼在公事以外兩人會時常回憶、談論“銀杏”時期的故事嗎?您如何看待這一段青蔥歲月?
文:我1986年7月分配到大理電視台,郭文平分配到大理醫學院,錢映紫分到大理師範。那時候的電視台是“新興媒體”,是時代的寵兒,但是文字工作者奇缺,我辦欄目時人手不夠,就請郭文平、錢映紫等來參與客串文字寫作,他們倆都先後調進了電視台。後來郭文平和我一起當了副台長、再後來他當台長我當總編輯,我們把一生都獻給了新聞宣傳事業。當然閑暇時我們偶爾也會懷念一下大學時代那段青蔥歲月,就像一首歌中唱到的:“想起了你,如此美麗,想起了你,如此遙遠”。
采訪者:在文學社期間是否仍有遺憾,是否仍有想做卻沒有做成的事情?如果給你一個機會回到那時候,你會如何做?
文:哈哈,回不去了。如果能回到過去,我可能會成為在于堅之下、與雲南幾個重要詩人比肩的詩人。
采訪者:以今天的角度來看當時(銀杏文學社時期)您自己的詩歌創作,您如何評價?您認為有哪些東西是您今天的寫作已經不會有的?或者換一種問法,您認為自己後期的創作和大學時期創作的最大不同在哪裡?
文:今天翻看《銀杏》,的确有一些文字顯得很稚嫩,缺乏曆練打磨。但是所有的文字無不是那個時代我們那群人心靈火花的記錄,真真切切,有青春的憂傷彷徨,也有時代的昂揚奮進。八十年代是一個崇尚文學敬重大師的年代,寫詩成為當時的流行時尚,詩歌的荷爾蒙在大學的空氣中彌漫,銀杏樹金黃的葉片上留下了多少少男少女真情告白。而今已經年過半百的我,自覺身心俱疲,詩意消失殆盡,隻能在回首銀杏文學社的往事中找回一點點詩歌的靈光,依稀看見缪斯女神在遙不可及的山巅向我招手。

《銀杏》會刊(圖片來源:謝竺軒提供)
采訪者:在詩歌創作中,您是否有過停滞的現象?覺得似乎靈感消失了,沒有詩情了?您又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文: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我一直忙忙碌碌,大量的精力都耗在寫作電視新聞稿和解說詞上,新聞的采寫與現代詩歌語言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久而久之,缪斯女神離我遠去了。2003年,我被安排到省委黨校離職學習一學期,學習之餘,萌生了重操舊業寫詩的念頭,在手機上用手寫筆劃了20多首詩,遺憾的是後來手機砸爛了詩作也随手機屍骨無存。回到單位後我又在新浪網上開了博客,寫下了一些心情文字,而繁重的工作和各種會議讓人無法做到心無旁骛,最終我的博客還是沒有堅持下來。
采訪者:現在文學社成員仍然保持了對文學的熱愛之情,仍然有很多的社員努力創作,作為前輩,您想對他們說些什麼呢?
文:文學之路“路漫漫其修遠兮”,隻要堅持堅持再堅持,任憑風吹浪打也初心不改,一直持之以恒寫下去,即使成不了于堅,能夠修身養性完善自我也是一種“活”的境界。
采訪者:好的,非常謝謝老師,老師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