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
——張稼文訪談錄
采訪人:鄧萦夢、畢曉蕾、房夢蝶
整理人:畢曉蕾、鄧萦夢
時間:2021年4月14日14:30—16:10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新聞中心
鄧:張稼文老師您好!
張:你們好,你們都是雲大的學生嗎?
鄧:是的。這是畢曉蕾、房夢蝶,我們三位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學生(研究生)。很高興能夠采訪您。
張:你們能說一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采訪嗎?
鄧:我們會對原來銀杏文學社一些非常重要的成員進行采訪,采訪之後形成文字稿,對當時銀杏文學社的概況以口述史的形式進行再現、述說和資料保存。
張:那我順着這份提綱和你們交流,有些細節記不清了,但是有一些資料還保留着。
鄧:好的,老師,那請您說一說您加入銀杏文學社的初衷吧。
張: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問一下你們三個,你們愛不愛好文學,寫不寫東西,有沒有發表過,以及為什麼想要寫東西呢?
房:我寫散文,而且在學校裡面發表過。有時候一個人會突然湧現一種情緒,而且伴随着想要用寫作來把它記錄下來的沖動。其次,按部就班的生活會讓人感到枯燥,每當到這種時刻就會想要靜靜地坐着寫作,比如簡單進行狀态總結等。
畢:我寫小說,但是沒有發表過。為什麼要寫東西?對我來說很簡單,就是因為喜歡。當有靈感以後,我就會好好構思,接着開始寫。
鄧:我會寫日記。
張:其實問“加入文學社的初衷”,說“加入”其實并不準确,因為我也參與了文學社的成立,所以應該問“你們為什麼要成立文學社”更加合适。我的這本《陽光燦爛——60年代生人的青春祭》(以下簡稱“《陽光燦爛》”),就是以80年代我們在東陸園讀書以及成立銀杏文學社的經曆為素材寫成的,幾乎每個細節都是真實的。因此,你們要問的幾乎所有問題,其答案全部在這書裡。因為涉及到80年代的中國的現實狀況比如物質匮乏、年輕人渴望精神解放、讀書等,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稍後返回再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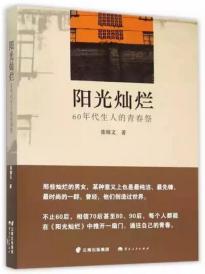
《陽光燦爛——60年代生人的青春祭》(圖片來源:張稼文提供)
鄧:那您在《陽光燦爛》(P7)這本自傳體回憶錄中提到喬傳藻老師的《寫作基礎》這門課,這是您在大學的第一門課嗎?那麼您在大學印象最深的一門課又是什麼呢,為什麼?
張:當年我寫《陽光燦爛》的時候,我收集了很多資料。(我到過)雲南省圖書館翻閱資料,還找過一些朋友(幫忙)回憶,也借過他們當年的資料。喬老師教的課,我印象中大概就是第一門課,在會澤院112教室。

(20世紀30年代的會澤院教室 圖片源于網絡http://www.archives.ynu.edu.cn/info/1021/2071.htm)
張:大學印象最深一門課是什麼?這個我不好回答,如果要回答,那喬老師的課算得上一門,喬老師的原型是喬傳藻老師。(印象深刻也包括對課程感興趣和不太感興趣的情況。)有一位講民間文學的朱老師,當時我很後悔報了他指導的一個興趣小組,因為我不太理解他講的圖騰這些東西。當時還有位老師,凡是不上他的課,缺勤了,他大緻就會讓你不及格,當時覺得不太喜歡。教《莊子》的是陳紅映老師,他已經去世了。教當代文學的是楊振昆老師,我們系的系副主任,同時也是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那時候隻有中文系,沒有學院這種說法。有一位老師講《紅樓夢》,那時候我還沒有讀過,聽不大懂也覺得枯燥。還有一位就是趙仲牧老師。而且我還把我大學時候的作業找出來,穿插在我的這本書裡。這份作業講“陰柔之美”,這份大概是張文勳老師或者其他老師留的作業,講文藝美學的。張文勳老師是我們中文系的老主任。我記得班主任,還有一個是姜老師,他應該退休了,據說他是姜亮夫先生的後人。《陽光燦爛》(這本書)可以供你們參考的是:它以某種視覺努力地還原了當時的現場,(這也就間接回答了一些細節問題)。總之,我對當年的很多老師都有特别的印象,也心懷感激,那些(讀書的)日子确實值得珍惜。
鄧:在整理文學社曆史資料時,我們發現于堅老師的“詩人要像上帝一樣思考,像普通人一樣地說話、生活”後來成為文學社的宗旨,您怎樣理解他的這句話呢?
張:我記得文學社創辦之初,并沒有正式的宗旨。當時大家都能背誦于堅詩作中一些精彩的句子,有時傳來傳去,就有幾種略微不同的版本。于堅高我兩級,大我十餘歲。他家在省城,家境不錯,從小就能讀書,有書讀,之後在工廠當工人,這些物質條件、社會經曆都比我們這些連油條、面包、火車都未見識過的人豐富得多。物資匮乏的年代,沒有書,連要張白紙也很難,就算去買,也可能買不到紙。文學社創辦之初是三中全會剛剛結束的時候,農村開始包産到戶,漸漸能夠填飽肚子了,城市開始恢複生産。那時,我們還在最基礎的層面,而于堅已經站位很高很高了,我們什麼都不知道,而他早就讀過泰戈爾了。回到于堅的“詩人要像上帝一樣思考”,因為當年的文革結束以後,我們國家裡面存在一些“假大空”的、“左”的東西,禁锢行動、禁锢思想,什麼都不能做,什麼都不能說,更不能想入非非,這是社會對人的限制。那麼“像上帝一樣思考”,我的理解是,類似蘭波所說,詩人應該是通靈者,類似先知。“像普通人一樣說話、生活”就好理解了。因為過去文字屬于上層社會、知識分子(這一小部分人),從來不屬于勞動(人民),隻有在文革前放衛星,文革期間寫大字報(才偶爾能夠接觸到文字)。我們當年如果見到文字,能看見自己的名字在紙上出現都是激動萬分的了。于堅提出“像普通人一樣說話、生活”,可以說是一種反抗。
鄧:您在《陽光燦爛》中經常提到文學社組織的一些出遊活動,而這些活動經常是以遊玩為初衷,但最終變成了文學問題的探讨活動,這是文學社組織活動的常态嗎?是否可以理解為文學社的文學活動起初并沒有嚴格的讨論主題,而是在遊玩的過程中自由發揮的結果呢?
張:我覺得這就是當年我們文學社最大的魅力。當年的我們正值青春、滿懷想法。滿世界找答案,到圖書館找答案,大街上找答案,跑到山上找答案,看日出找答案。熱愛文學,于大多數那時的我們而言,這些活動像一種心智啟蒙,而不是專門為了搞文學訓練、當作家。
鄧:根據您在書中的描述(P86),銀杏文學社最初的文學創作并不是以正式的刊物發表而是以壁報的形式展現出來的。當時壁報的辦理是由誰經手的呢?如何分工?壁報畢竟是面向全校師生的,在辦理前内容是否要經過校團委或者宣傳部的審核呢?
張:什麼算正式刊物呢?正式刊物的成本很貴,那個時候條件很艱難。在我們之前雲大有個很出名的文學社,叫“犁”,刊物才出了一期,就被消滅掉了。到82年,和銀杏文學社成立之初同步的,是于堅他們弄了一冊《高原詩抄》,是手刻蠟紙油印的小冊子,那時候我們都激動得不得了。壁報的位置在銀杏道和鐘樓下面的道路交叉處的東北角,有個十字路口。而我們的壁報是用手寫體抄上去的,當時于堅的字寫得好一些,還有就是蔡毅。當時我們壁報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現在的一些正式刊物。
房:老師,手抄報(指手抄壁報)就是于堅老師一個人辦嗎?你們都不參加嗎?
張:我們參加的,到處去号召。過去是不一樣的,過去有什麼好東西,都是互相傳抄的。
房:那您記不記得辦了多少期?
張:這個我記得不太詳細,大概三期左右,不太長,但影響巨大。影響大到,就是後面一期要開始了,我們都舍不得把前面的撕了,都是完整地揭下來。房:那報紙會在那裡放多長時間呢?
張:随意放置,沒有周期。基本征稿了,成一期了,那麼就出一期。辦壁報就是由于堅、蔡毅他們寫、他們抄。他們抄在壁報上,學校裡面的很多同學又來圍着抄壁報。理論上,這些是要經過校團委或者宣傳部的承認。所以我在書裡專門講到銀杏文學社的誕生,它是雲大所有社團裡面誕生最難的一個。
鄧:文學社在發展的過程中第一次面臨解社的危機(P99)是由于什麼原因,當時社員們如何看待戀愛和文學社之間微妙的關系呢?
張:這個問題我覺得問的角度不太貼切。第一,文學社沒有面臨解社的危機。因為《陽光燦爛》是一本小說,面臨危機,确實是對當時而言的,但是我用在我的書上,也沒有任何的誇張,隻是說把它的進度推進到文學社最核心的階段,放大了這個情節。(就像在書裡)我說到圓通山開批鬥會,那隻是一種戲劇性說法。這不是一種誇張,而是把進度進一步推進。當時對于當事人而言,确實是很頭大的一件事情。我們沒有發展得很壯大,但是我們最重要的人,要亂出這類事情來,當然是很麻煩的事。像當時的劉夢軒(書中的人物),他還年輕,并沒有這種生活的智慧來解決這些事情。“當時社員們如何看待戀愛和文學社之間微妙的關系?”這個幾句話說不清楚,《陽光燦爛》也在探讨這個事情,這本書探讨的主要是成長主題,成長主題中最重要的就是青春,以及關于青春期如何個人社會化的問題,當事人如何看待其實在書中也提到了。
鄧:您在書中第119頁提到的102舍刊《星星草》是不是可以看作《銀杏》的前身,能否為我們詳細講述一下刊物選作的标準及最終刊印、發行的過程呢?
張:這個不算。雲大的新時期文學在三中全會以前就開始了。那時候我們是很出名的。“銀杏”文學社也好,前面的“犁”文學社也好,都是一脈相承的,都是一代一代,一級一級的。我記得就是85年,我和朱紅東兩個人就到會澤樓上校黨委宣傳部,找黨委宣傳的部長史宗龍老師。他是搞文藝理論的,我們想得到他的支持。當時在中文系,其實還是有阻力,因為我們總支書記對銀杏文學社及《銀杏》總是不大放心不大支持,幸好是系主任這些領導和老師支持我們。後面由校黨委宣傳部支持我們,還批給了我們一筆“巨資”,是50塊錢。同時,就開始用當時的打字機印了雜志。
鄧:當時就已經有打字機了嗎?
張:那個其實也不叫打字機,叫撿字,鉛字排版印刷。我也做過記者工作,體驗過撿鉛字的工作。最後告别這個是在89年底,在青年路。
房:那你們成立那天有些什麼活動嗎,比如布置會場或是别的什麼慶祝的活動,以及邀請一些人員?
張:這些都有,全部寫在這本書裡面了,可以對應到具體的人,隻是不能夠照搬式引出來,因為這不是回憶錄,這是小說。
鄧:據了解,當時銀杏文學社并不隻是孤立地在雲大内部運行和活動,也和昆明其他高校的文學社一起活動,如昆明師範學院的《奔流》《一多》、雲南民族學院的《野草》《遠方》等,您能講講當時共同舉辦的活動以及最終有什麼成果嗎?書裡面講了一個“紅五月”高校詩歌朗誦會,想問問您還能回憶起除此之外的和其他的高校在一起辦的活動?
張:我在大學的那四年,當時高校的文學社還是非常多的,能夠點得上名的,包括在社會上的,比如84年或85年改名師大的昆明師院,他們當時較出名的詩人是彭國良、劉楊、陳慧等;我們這邊著名的就是以于堅為主。大家各有千秋,即使風格是不一樣,但是互相是一定來往的。大家就是要靠思想碰撞,靠互相不同的意見,才有靈感,這個是我覺得當年最珍貴的事。當年我們常常向同學借飯票。我和雷平陽當年就是通過社團文學交流認識的,他在昭通。我們搞的活動,比如說“紅五月”詩會、朗誦會,就在東二院食堂的樓上,文學社還沒有成立就已經開始搞了。學校之間的民間交往實在是太頻繁了,就像是大江大河一樣,所以大家就是瘋狂讀書、瘋狂交朋友、瘋狂思想。這個時代是當年最珍貴的事情。當年,其他的也有,但是我跟我朋友經曆過這些的人,各有各的個性,大家都不是一定要為了當作家(可能很少的人是有目的,有他的思想和事業性)。但是我們當年根本不是,我們隻是為了想要認識社會,作為一個成年人尋找自我。因為當年是沒有“自我”這個詞的,“自我”這個詞是我們之後才有的,誰敢有“自我”?不可能的事情,聽都沒有聽過這個詞。這些活動當年有很多,比如說和昆工,我和昆工的葛躍,他當年是昆工原上文學社的社長,他學自動化,貴州人。我們兩個編了一本《雲南省大學生詩選》,鉛字印刷。有什麼成果?我覺得成果太多了。當年雲南高校的詩歌運動,主要是詩歌,也包括有其他文學,基本上是影響了昆明地區,也影響了全省,同時在全國都是風起雲湧的,就文學而言我們不是邊疆。當年還提出紅土詩派和“橫斷意識”,隻要你找到當年的銀杏雜志,還有在市文聯的《滇池》雜志,這些上面都還有。我覺得以銀杏文學社為主的這些社團,當年最大的功勞,就是讓我這樣的人好好成長,活下來,活到現在也是一個真誠的人,這個就是我自己最大的個人收獲。到現在讀到好文章,内心還會感動。經曆過社會這麼多事情,我是當記者出身,也看過各種各樣的事情,有些時候有些事情完全可以讓你灰心、絕望、随波逐流,但是,因為我經曆過銀杏樹下這段時光,這就太重要了。估計到目前為止,我們裡面這些人,這些朋友裡面進入爛泥坑的,成為很俗氣的,似乎還沒有或沒有聽說。銀杏文學社的經曆,或當年高校文學運動的意義?要說有什麼收獲或意義呢(這種收獲或意義并不是做台賬、做績效這類的),首先是讓我們成長,活下來,身心健康。我覺得這個是萬幸,這個是第一。第二,推動整個雲南地區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最先在校園,全國都一樣。如,一二一運動。這些最先鋒、最先進的思想,實際上都是先從校園開始。我們有幸成為了那一群人。第三才是文學,我這本書裡面都寫到了,首先是武器,對付那些陳舊腐朽的東西的武器。
鄧:書中(P136)有提到在于堅老師和朱紅東老師即将畢業、退居二線之後,您被推舉成為文學社的主幹,當即對文學社進行了改革,有了正式的章程以及一些如會員證等更規範的規定。那是否可以理解為在那之前文學社的管理是處于一種“自由”和“即興”的狀态?
張:是的,後面我們确實是“自由”和“即興”的。第二是這個社團有了正式的章程、社員證等等這一些,但這個不能說是“過去是自由,現在不自由”的意思,實際上是因為隊伍更壯大了,當時最大的事情就是思想解放,最難的事情是思想不解放,什麼都做不了。年輕人的聲音更多了,“不準你這樣”“不準你那樣”的聲音開始弱下去了。
鄧:當時文學社也經常會有校外的人員來參與活動,例如您在書中提到的周良沛先生,這些校外人士是如何得知銀杏文學社的活動信息的?是否有人引薦或者當時文學社的影響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校外人員入社的情況多嗎?
張:這個是存在的,從我們文學社這一塊而言,像于堅他們和他們本來就認識,而且那個時候思想解放,各種大河奔流,在那個年代這種交往很正常。到我和文潤生(朵美)的時候,于堅他們是81級畢業,以後就交到我們82級。我們是梯隊形的,然後到83級這種下去。當時銀杏文學社像于堅也好、朱紅東也好,他們雖然出去了畢業了,但是還會回學校。一個是因為我們需要他們,畢業後我們就請他們做校外(理事)。校外人員入社的情況,一些人本身就是校外的,我們就請他們做理事、顧問之類的友情角色,但是不算太多。

(周良沛先生 圖片來源:張稼文提供)
鄧:您在書中經常有提到當時社員們的一些詩作,甚至具體到詩句,您是如何做到如此真實地記錄的?或者說是這些詩作您還保有發行稿?是否可以拍照記錄?
張:我當年有寫日記習慣,還有個記錄的筆記本。當時聽到朋友們的有些話,就會拿本子寫下來,所以我在這本書裡面引用了當年寫過的原文,這個是一類材料。還有一類材料是《銀杏》當年雜志上的。第三類是個别通信的信件。這些是很珍貴的,因為他們自己都沒有,包括于堅當年寫過的這些。所以,這些老的東西還是值得好好地珍惜,也建議你們現在的東西不要輕易丢掉。
鄧:銀杏文學社期間,您最志同道合的朋友是誰?在創作方面,你們會互相影響嗎?
張:簡單的說,最重要的就是于堅、朱紅東、文潤生。就當年而言,我們是幾乎天天互動,天天在一起,有空就泡在一起。我們開會都是天一句、地一句。當年于堅還會請我們下館子。創作方面互相影響這個不太好說,但是當年像以于堅為代表的這些人,(創作)已經比較成熟,對我們影響非常非常大。不隻是對我們這些人影響非常大,就是對普通人影響也非常大。當時很多東西都是手抄本,都是自己抄。所以我說他們是志同道合的人,包括蔡毅也好,我們都是好朋友。
鄧:您在書中經常提到文學社的女性詩人如“大眼睛”“羊角辮”“青魚”等,她們充滿靈性和活力,總是迸發出青春所特有的激情。您能講講她們在文學社時期的創作嗎?
張:你講到的這三個女學生的人物原型都是我們班的,當時真正有文學思想的人其實都不多,很少。于堅是最典型、最成功的那一個,到現在都是。裡面還有些人寫小說,他說他要把他名字跟王蒙、劉心武排在一起,那個人在疫情期間已經去世了。全身心來寫作的人沒有那麼多,都是年輕人。我想問你們都是多少歲讀大學的,有20歲?
鄧:我讀大學的時候是19歲。
畢:我18歲。
張:于堅80級,到了81級也還有。到了我們班一溜兒,他們是成年人,我們級基本上都是娃娃,未成年的娃娃,我是17歲,我們班最年輕的女生16歲,16歲能懂得什麼,所以我們都是迷迷糊糊的。聽到一個故事,讀了一首詩,就像泰戈爾,讀也讀不懂,隻是覺得美得很。很多人主要是玩,讀什麼書、唱什麼歌、跳什麼舞,基本上都不是專門寫作的,當然,大家也還是寫。我們班當年是八十幾個人,女生占了一半多,個個都有才氣。你看這(指《陽光燦爛》)裡面寫到的“老虔”,錢映紫,她在大學一年級寫了一篇《小雨點》,被喬老師看到了,就當着全班讀這個作品,讀完就推薦這個作品,它被收進了全國女大學生作文選。

《陽光燦爛》書中的人物原型(圖片來源:張稼文提供)
鄧:您還記得這些女孩子她們創作有沒有某一個人寫哪一種文體,寫得更好?比如說哪個女生寫小說寫得最好?哪個女孩子她寫詩歌寫得最好的這種情況?
張:比如那個“老虔”,錢映紫,她散文寫得最好。“羊角辮”是詩歌寫得最好。當年我們班還有王英,現在是在臨滄學院的老師。當年個個都寫得好,寫得讓我們男生眼前一亮。等着她下一篇,而到下一篇就不寫了,基本上都是這個情況。
鄧:您在銀杏文學社發表的處女作品是什麼?您能分享一下寫作它的過程嗎?
張:這個我記不住了。這個問題看要怎麼表述,是在《銀杏》雜志呢還是文學社成立以後。當年我們班上發表文章都不算多。我還算比較愛好文學,但是我基礎比較差。當年我與文潤生,他文字比我強,就他當主編,我當社長,做行政、組織這些工作。當時發文章的人不算多,一個是發東西很難,發校報都很難很難。我自己發的第一篇,也就是書裡(《陽光燦爛》)裡寫的喬老師推薦給《學寫作》小報發的。那時銀杏文學社還沒有成立。稍後還有一小篇甘肅蘭州的一個雜志上。
鄧:是不是《飛天》?
張:不是《飛天》,《飛天》我是85年(1985)以後才在上面發表作品。我個人寫作的東西比陳凱差遠了,第一是基礎确實很差,不是謙虛。小時候沒有見識,也沒有條件。
鄧:主要是你們那個時候在文學社開始密集寫作的時候年紀還很小。設想我們16、17歲讀高中的時候基本上不寫東西,也有這個背景。
張:那還有第二點就是模仿,拼命模仿。閱讀不夠,經曆不夠,你也模仿不了多少,但是模仿在那些年太重要了,那個過程太重要了。你要說寫作過程,那根本是沒有,不可能有正兒八經的寫作。
畢:是一個比較松散的狀态。
鄧:那您寫完東西之後會有意識地去修改它(作品)嗎?還是說寫完就放在一邊了?
張:兩種可能都有。大家寫東西時候大都是躲着的,都不告訴别人,寫東西要安靜,但找靈感的時候就是最鬧的時候。
畢:她提的這個修改問題,我自己有個習慣,比方類似于詩歌這樣一些高度即興或者抒情的東西,按我的習慣寫出來就不改,甚至都不看,都放着好長時間才翻出來。但是像小說,我就會一遍一遍地改,因為它好像細節更多。
張:不過是兩種不同的人,實際上好的作者多的是。我最近重讀了《百年孤獨》,太感慨了。之前我是在八十年代末看的,讀馬爾克斯,包括卡爾維諾。當時,覺得太神奇了,讀又讀不懂,又沒有那個背景,印象非常深,就覺得太好玩了。重讀了一遍後,發現書裡全是詩,太精彩了!
鄧:您的故鄉對您的寫作有影響嗎?是怎樣影響您的?當時的銀杏文學社有沒有存在同鄉一起創作的現象?存在的話,大家在創作上互相會有怎樣的影響?
張:這個,我覺得故鄉對每個人的寫作的确有影響,相當大。但是看你怎麼看故鄉,我的《江邊記》,是一個安慰,也是我獻給家鄉的故事。故鄉跟童年,對我太重要了,實際上我在《江邊記》中也提到了很多觀點,這個(拿起《陽光燦爛》)實際是我最瘋狂、最外向的時候,但是我人生最重要或者說更多時候實際是内向。

《江邊記》書影 (圖片來源:王雲杉提供)
畢:這個書裡面其實一開始也提到故鄉的影響,您帶着故鄉的一些東西來到一個新的地方,體現出的一個狀态。
張:我是86年大學畢業,到報社當記者,開始對農業農村和故鄉有一些反思,也經常跑農村。還寫了首詩,鄉村沒有任何田園和任何詩,鄉村隻有酒鬼,所以我從來不寫田園牧歌,雖然我是從農村出來的。但我覺得故鄉非常非常重要,故鄉對我影響最大就是“萬物有靈”。我小時候很孤獨,就跟植物對話,放豬跟豬說話,看着鳥叫,雖然聽不懂,但就是覺得很好聽。很多時候,在人生當中、人際當中,進入社會排解不了很多東西,你就看看山、讀讀書,就過掉了。我是大理人,當時銀杏文學社大理人很多,郭文平、文潤生、錢映紫等等。但是大家沒有一起創作,從來不一起創作。我和文潤生雖然都是農村出來的,但是我們兩個風格完全不一樣。但隻有一樣相同,就是瘋狂讀書,如饑似渴。
鄧:哪位詩人的詩歌(作品)對您有影響?他是如何影響您的?請具體談一談。張:這個是講過去、當時還是現在?
鄧:都可以,這個沒有時間段的限制了。
張:在當時來講,我們讀大學之前,讀到的詩歌基本上是報紙上的,廣播裡面就是假大空那些東西,很通俗。來到昆明城也基本是這些,凡是主流的,學院的也好、社會上的(主流的)也好,都是這些假大空為主,凡是清新一點的東西,一出來可能是要死掉的。不斷地死不斷地死,總還是有活着的,慢慢像《野草》(非魯迅先生的)這樣的東西就多起來了。雲大為什麼要成立銀杏文學社,它起點為什麼這麼高?高是因為有于堅這類人。他來找我們,說“現在的詩歌太舊了”。雖然我們聽不懂,但還是跟着上。對我而言影響大的,在銀杏文學社開始前是泰戈爾,他的文學語言的魅力,簡直想不到。過去我們隻覺得,來昆明之前就是“床前明月光”這種,但是突然看泰戈爾一下子被吓住了。還有海明威,雖然是小說,但直到現在我都特别喜歡。弗羅斯特這個詩人,我在大學時期恰恰不喜歡他,但大學快畢業的時候喜歡他,到現在我都是他粉絲。有太多太多了(指有影響的作品),我讀的更多的還是國外的。當時身邊的詩人就是于堅,還有其他人,那些朦胧詩人:北島、顧城、舒婷。隻是,我覺得身邊影響最大的還是于堅。
鄧:在什麼樣的狀态下您會願意寫詩?我想知道,當一個事物刺激到您的時候,您在情感飽滿的狀态下是否會立刻寫詩?您的“情感”有沒有冷卻的過程?
張:這不太好回答,我基本沒有好好寫過詩。在當時寫東西都有很多感觸,但是不知道怎麼寫,寫不好,很多都是靈感突發。蓄謀已久、老謀深算地構思很久,當時還不具備這種能力。靈感來了一個晚上不睡覺,逃課就開始寫了。寫的基本上都是廢品,大部分都是。
鄧:您如何看待詩人與讀者之間的關系,有評論家将詩人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刻意保持與讀者的距離來增加詩歌及詩人的神秘感從而增加閱讀感受,另一類則和讀者親密互動從中吸取有益于詩歌寫作的建議;您傾向于哪一種?為什麼?
張:所謂“詩言志”,站在我的角度,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有些人是職業作家,以寫作為生,但我基本沒有這種感受,因為我不以此為生。準确說角度不太一樣。當時沒有說一定要靠寫作搞點稿費,根本沒有這麼想過。
鄧:您在寫作過程中會産生焦慮嗎?您能不能談談寫作過程中的焦慮問題?
張:這個是講現在嗎?
鄧:她後面這幾個問題都是講現在,主要是講現在。
張:這個要看你怎麼理解,我覺得很為難。有時候想寫東西寫不出來,不知道怎麼開頭。因為我是屬于業餘作者,跟那些專門的不一樣,大概最缺的是精力,主要是沒有時間。寫東西是要花時間的,尤其是自由寫作,不是命題寫作。所以前幾個月,那個《散文詩》雜志約了我稿,上世紀它發了我很多很多,包括頭條這些。(他們)要求我寫一點寫作體會,其中跟你們也有點相近。很多人有個想法,想寫,但你不知道怎麼開頭。你不知道開頭第一句,第一句寫出來就解決了。實際上包括陳凱那篇《把油藏在米飯裡》,我一讀就被陳凱吸引,他有個細節,但我覺得也不十全十美。尤其在虛實之間,還有心理,那種裝作很老到的心理描寫還是吓到我了,在網絡上一般很少讀到這種東西。所以我覺得寫真正的東西是非常需要花心思的,而且一定要摒棄眼前的功利目的,長遠有可能有功利性,但是短期要(摒棄)。我最讨厭的文章是什麼呢?譬如《人民日報》《大地》副刊上的不少文章我都不喜歡。所以你說的寫作焦慮一定會有,我喜歡一個人走路,清空腦袋,或者有困難的時候就一個人走路。很多時候走着走着,想着一句話馬上就沖回去寫了。我也沒寫什麼大東西,寫作首先要内心自由,第二,一定不要拘于眼前的任何功利,眼前的功利是你焦慮的原因,根本不需要去(想)。
鄧:您滿意現在的生活狀态嗎?能說說當時和你一起的銀杏人的生活狀态嗎?大家還在創作嗎?
張:要我回答保證說滿意,确實很多層面上我是滿意的,從世俗常規上,我們到退休的年齡了,我還活着,至少還身心健康。第二,和滿街的人一樣,基本上衣食不愁。第三,我還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退休了就有時間去養花種草,去寫文章,去做事情。第四,是我十五年來一直在互聯網戰線,他們說我是省内在互聯網一線很老的工作者之一,還天天在跟年輕人在一起,全是互聯網,媒體的、産業的,我覺得自己還不老,從這個層面上很滿意自己的狀态。唯一最焦慮的是就是時間不夠,自主、寬閑的時間不夠,就是需要讓腦袋放松、閑下來,更多的自由。(當年的銀杏文學社成員)我了解的整體(生活)狀态都還好,隻是相互來往不多,非常熟悉的非常見不得的事情在銀杏人身上我還沒聽說。從世俗的角度大家過得都還不錯,但是大部分人都不寫東西了。他們中好多人,包括文潤生,别人去采訪他們都說已經不寫東西了,大家(馬上都到退休年齡了)說不準又想寫起來,又燃起創作夢。據我所知大部分人都沒有寫了,或者有人悄悄寫,沒有拿出來。

張稼文《那些小事情》(圖片來源:王雲杉提供)
房:這就“不可考”了,哈哈。(衆笑)
鄧:您想對現在仍在堅持創作的“銀杏人”說些什麼呢?
張:現在雲大的“銀杏社”是什麼情況?
鄧:“銀杏文學社”現在我們(采訪小組)是沒有在裡面的,社團是本科生在管理。現在情況就是,成員基本上來自于文學院内部,比如說物理學院、化學學院這些我們學院外的加入文學社的不多。然後另外一個情況就是現在文學社比如說舉辦一個征稿活動,大家很難自主地去投稿。大家來投稿都是因為文學院或者說學校承諾給得獎的人進行獎勵,這樣大家才會去投稿。所以這也是現在文學社發展不下去、不能更深一步發展下去的兩個很大的問題。但是也有人還在堅持寫東西。
張:就是不多?
鄧:對,不多。
張:所以我個人覺得銀杏的精神要傳下去,這種傳承太重要了。現在學院是哪個老師在當院長?
鄧:院長是王衛東。
張:原來是段老師,段炳昌。因為我覺得關于銀杏文學社的精神,還是可以不斷地去繼承發揚。首先來說,思想上要獨立思考,不要同流合污,這個是最重要的。獨立思考,拼命學習,拼命吸收各種各樣的營養,千萬不要相信什麼國學,千萬不要相信這些事情,尤其搞文學這一塊兒的,對于中國人而言,還是要加強科學思維、各種思維的磨練,這個非常重要,否則你寫不出來好東西。所以我覺得雲大銀杏社精神,就是“叛逆”精神、先鋒精神,人要進步,永遠要自我“揚棄”,不要趨炎附勢,去做權勢的走狗。文學它是關乎人心、人性的。它不是外在的空的,文學“無用”,它為什麼“無用”?因為人有各個層次的需求,一定要有更高追求、更高境界。文學的作用在這一點:提醒我們人生還有更多境界。其實我早就已經告别文學,因為工作的原因,包括搞這些活動。現在喜愛文學的人太少了。第二個,在基層的人太多了,就是忙着發表東西,網上發、紙刊發,有的基本上天天寫天天發。這樣下來,(那)他哪有那麼多時間讀書啊?他哪有時間工作啊?他哪有時間采風啊?所以我就感覺有點遺憾,年輕的、上歲數的在基層比較多,但是都是忙于寫東西發表成名,意思不大。既然人生還有更多更高的境界和要求,你要靠寫東西去養活自己,你就要有個好工作,隻有(有好工作)你才能在業餘時間寫作,這很重要。銀杏的精神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由,一定要自由。你要有自由的心态,同時要有個開放的系統,不斷去接納新東西。現在《銀杏》雜志還在辦嗎?

2014年《銀杏》雜志(圖片來源:謝竺軒提供)
衆:在辦。
鄧:前兩天還征稿了,面向全校師生征稿。
張:征稿的主題是什麼呢?
鄧:它沒有主題,但是它限了文體,詩歌、散文評論和小說。
房:這是一個相當于“百年中文”的系列活動,而且還是學院内部的,都沒人參加。現在就是到這種地步,寫東西的人特别少。
張:我個人覺得你們三位女同學可以好好練一下筆杆子,太重要了。我跟他們經常(應該是同事)講練好了筆杆子什麼都不缺。我八十年代末當記者,就天天跑,當年有個詞“萬元戶”,相當于現在上百萬。當年都是很成功的人士,但是我到新千年之後再看,這些人大部分消失了,有些人又甚至陷入貧窮,有些人進了監獄,有些人當年生意很好但是他不知道世界已經變了,但是靠筆杆子為生的不少人還在好好地活着。現在又過了二十年,互聯網又把整個社會改變了。
房:我們昨天采訪于堅老師的時候,他談到銀杏文學社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是一下子就成名了,它是慢慢的過程,雲大會和其他外省的高校有交流,比如說西藏大學和重慶大學。但是他(于堅)記不太清楚了,隻想得起這兩個大學。您有沒有這方面的記憶?就是你們和其他外省的高校有什麼具體的交流嗎?
張:更多我也記不清了。和你們的理解不太一樣,因為當年很多管理不太一樣。當年我們和全國每個省,好像除了西藏(都有聯系)。首先是通信,不是官方的聯系,而是以個人形式。比如說今天北京哪個社團的(人)來了,我們就接他吃一頓、聊聊天就完了,到後期畢業以後,就正式一些。走入社會之後官方的更寬容,就經常請他們來講課。當時沒有那種官文、官章,都是一拍就定了。稍微有條件的就出門交流,基本上都是這種形式。
房:那他們來了就住在你們宿舍嗎?就住在東二院嗎
張:對啊。裡面有很多很多麻煩,錢是最大的,(我們)墊了各種證(證件),就是各種“窩藏”。
鄧:現在我們沒有交流的一個原因就是高校之間壁壘很嚴重,互相不交流。
張:我個人的思考,就是這些年雲大關于文學社,前幾任都還有聯系,有點奇怪。于堅也跟我說過。我記得我還在銀杏社的群裡,每個人的頭銜職務都很多,好像配比得非常完善,這是一。第二呢,我個人覺得現在網絡時代恰恰讓人顯得更封閉了。我個人覺得大學時候,一個是完成學業,第二個趕快看社會,怎麼生存怎麼生活發展,中文系文學院的同學更是。
衆:好的,謝謝張老師接受我們的采訪,辛苦老師。

張稼文老師與采訪同學合影留念,(圖片來源:鄧萦夢提供)

